科技界的自律与苏格拉底悖论
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
时间:2011年05月16日来源:科学时报
2010年底,《科学新闻》杂志发表了对著名科学家蒲慕明教授的访谈《中国科学“病”在何处》,蒲先生认为中国科学的核心病症是: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这需要科学家努力改变自己的科研态度和学术界的“传统”。解决办法是:科学家应当自律。该文一发表即迅速引起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广泛热议。客观地说,蒲慕明先生很多关于科学活动在微观层面的观点,笔者都同意,但是对于蒲先生在宏观层面给中国科学的病作出的诊断以及开出的药方,实在不敢苟同,我时常怀疑自律这贴膏药能否医好中国科学的“病”?甚至担心,如果按照蒲先生的药方医治下去,非但治不好中国科学的“病”,反而会贻误时机,最后病入膏肓,无药可医。
众所周知,一个成熟的社会依靠两套规则系统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行,即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法规与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风俗习惯、道德等规范来划定社会秩序。通俗来讲,现代社会对个体行为的规范,通常采取两种措施:自律与他律的结合。
自律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约束力量,它通过漫长的教化与训练,最终达到对个体行为的规训作用;而他律则是在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下,划定个体的明确行为边界,具有强制性,一旦违规将受到相应的惩罚。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自律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他律的实现则是无条件的,他律的存在是自律发挥作用的基础,否则自律就是一种善意的乌托邦。
正如在一个没有健全以及强有力的交通法规的环境下,个体再怎么自律也无法避免随时可能出现的交通危险。现代社会的各种监督机构以及制衡机制的大量存在,都是基于自律有时并不可靠的共识基础上建立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他律的存在暗示个体的违规成本将远远大于违规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理性人,选择自律行为将是所有行为中收益最大的行为。而当下中国科技界面临的问题却是他律机制的严重失灵与扭曲,进而导致约束自律行为的防线失守,从而出现以自律与他律机制共同维持秩序的格局开始出现大范围失范现象。究其原因,不难看出,自律机制的作用日渐式微的主因是他律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违规的收益远远大于违规的成本,坚守自律原则的个体在这种环境下,其收益将受损,这种现象促成一部分人也开始加入违规的行列,弥补其潜在的损失,而当下的科技考评机制又为这种现象提供了最后的推力。因此,中国科技界的最大病症就是作为体制功能的他律机制的失灵与扭曲。
中国科学界所患的疾病,已经不是自律所能解决的问题。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说:用道德观念去医治社会疾病不会像医治身体疾病那样有效。由此,笔者不禁想到一个哲学上的经典命题,即苏格拉底悖论,它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心甘情愿(或在知道的情况下)做错事。然而,遗憾的是,当所有人组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又总是在知道的情况下做错事。由此可知,仅凭自律来医治中国科技界的病,无异于隔靴搔痒。
为了说明当下中国科技界的“病”的严重性,先来看看科技界的盘子到底有多大。据科技部提供的信息,截至2009年我国共有科技人员总量4600万人,2008年R&D人员总量为197万,当年投入的R&D经费为4616亿元,占GDP的1.47%。试想,如此庞大的科技群体,面对着如此巨额的科技资源,仅靠共同体成员的自律就可以解决公平分配与秩序的合理安排吗?如果退回到19世纪单打独斗的小科学时代或许还有可能,但是对于20世纪以来的大科学时代则是万万不能的。迷信个体的自律以及君子国的独善其身没有错,只不过那是一种无害的怀旧的浪漫主义情结而已。面对如此庞大的人财物的合理配置,提供合法秩序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体制安排的各种他律措施。永远不要迷信个体的抗诱惑能力,我们宁可相信制度把人预先设想为自私的,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制度性防范措施的设计。这也是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一个经典结论。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的学界之所以还能拥有良好的自律表现,是因为那里作为强制性手段的他律措施还在良好运转。即便如此,也仍时常听到学术违规事件被发现以及被严惩的报道,更何况在他律失灵或扭曲状况下,自律表现将是何等糟糕。
另外,蒲先生认为:责怪体制而不检讨自己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对此,笔者也是不同意的,我们无数次检讨自己有用吗?每日三省吾身,并不能保证社会进步。更何况在当下批评某一项政策措施设置不当是有很大压力的,并非如蒲先生想象的那样轻松。蒲先生的潜台词无非是说,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平庸带来的罪恶,或者按照德国哲学家彭费霍尔的说法,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道德平庸固然可恨,但至少在科技界不是致命的。今天,我越来越开始相信,对于中国科技界危害最大的恰恰是那些无责任的罪恶。而无责任恰恰是他律失灵或者扭曲的一种表征。为了重建他律,对科技体制进行批判是无法绕过的山口,即便为了让每个共同体成员在自律的基础上都做一个有道德的自私者,也需要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毕竟自律不是免费的。
(上海交通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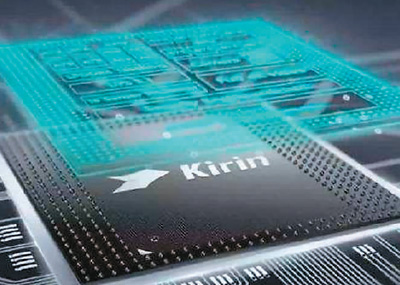
 001
001
 002
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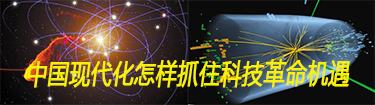 003
003
 004
004
 推荐席位
推荐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