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逐于智谋”时代的教育
2012-3-7 05:45 http://blog.sciencenet.cn/u/周可真 苏州大学哲学教授
古今中外的竞争,无论是“竞于道德”,还是“逐于智谋”,抑或“争于气力”,本质上都是人才竞争。
按精通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历史而深悉其竞争奥妙的韩非的人才观念,历史上各色各样的人才归结起来无非是三类:“道德之才”、“智谋之才”和“气力之才”。韩非本人是崇尚“气力之才”的,他的人才观是“得气力之才者得天下”的“霸道人才观”。与韩非的观念相反并且在当时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才观,是崇尚“道德之才”的儒家“得道德之才者得天下”的“王道人才观”。(《孟子·公孙丑上》:“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荀子强国》:“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王霸之辨”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论域中的主题,这反映出当时很少有人崇尚“智谋之才”,至少是“得智谋之才者得天下”的“智道人才观”远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实际上,整个中国古代在人才观方面的争论,一直是在“霸道人才观”与“王道人才观”之间展开的,“智道人才观”从来都没有登台演出的机会。
汉末时曾有过“才性之辨”,其中“才”实指“气力之才”或“霸才”,“性”实指“道德之才”或“王才”。到了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了关于“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二重人性论观点,二程继承并发展之,改称“天地之性”为“性”(又称“理性”)、“气质之性”为“才”,认为“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从本体论角度将“才”“性”纳入了“气”“理”范畴,并以“体用一源”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将“才”和“性”统一起来,认为“才”“性”之间是“性为体、才为用”的“体用”关系,强调了“性”对“才”的决定和统制作用。这种本体论范畴的人才观为朱熹所全盘继承,及至程朱理学上升为国家统治思想,它更成为中国正统人才观,只是到清代以后渐失其本体论色彩,并最终被俗化成一直流传至今的所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谚语式口号。
至今在中国占据正统人才观之地位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观,在哲学层次上并未超出程朱理学范畴,且其“德才”观念也还没有超出春秋战国时代“王霸”范畴,其“德”仍属于儒家“王道”范畴的“道德之才”,其“才”仍属于法家“霸道”范畴的“气力之才”。所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人才观的意义上就是“才性兼备,以性为先”,在政治观的意义上就是“王霸兼备,以王为先”——相当于西汉学者刘向所谓“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要言之,当今中国的人才观依然未出乎“王道人才观”和“霸道人才观”之范围,它不过是传统理学人才观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形式,其思想特点是“儒法合一”和“以儒为主”。
然而,最近三十多年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正统人才观实际上越来越偏离其“正统”轨道,而趋向于三国时期曹魏“新法家”——曾被许劭品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观。
但是,当今中国的用人之道虽然实际奉行的是“唯才是举”,而在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上却不及曹操之高。
首先,奉行“唯才是举”的曹操在政治上力主“法治”,他本人曾因触犯自己所定的“法”而采取自行割发的方式来表示接受相应的“法律惩罚”,这显示了曹操式“法治”的特点是“有法必依”、“令出必行”和“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除了“主公”曹操一人具有“法外”特权,其他所有人都不具有这种“特权”(他们若遇到类似曹操“犯法”的情况,无人可以用割发来取代杀头)。而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种种情况都表明,今朝之“法治”水平远不及曹操式“法治”水平,不但“有法必依”、“令出必行”做不到,“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更无从谈起,连“李刚”家的“官二代”距离“主公”身份不啻十万八千里,却也想享受到“主公”的“法外”特权——“我爸是李刚”正是由“李刚”乃至于其“官二代”所实际常常享受到某种“法外”特权这个“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按:马克思、恩格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自然地流露。
其次,奉行“唯才是举”的曹操在精神境界上达到了如此高度:其爱才如命,以至于能以海洋般宽阔的胸怀来对待“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今朝用人者,其谁有如是胸襟?“武大郎开店”的情况倒是司空见惯!
三国之争,最终曹魏胜出,是因为魏主曹操在传统政治的基本结构框架内真正做到了“唯才是举”——苛严的“以法治才”和真心的“爱才如命”。因当今中国政治的基本结构框架并未超出传统政治的范围,故实际奉行“唯才是举”的当国者,想要在国际竞争中最终胜出,在用人问题上,就至少应该做到苛严的“以法治才”和真心的“爱才如命”,否则决无胜算。
由于最近这些年来实际奉行“唯才是举”的当国之人在政治观念和政治境界上达不到当年同样奉行此道的曹操的水平,做不到苛严的“以法治才”和真心的“爱才如命”,这就难免要出现如汉末之曹操那样的“乱世之奸雄”:他们有“霸道之才”,却无“王者之气”,唯惧“严刑峻法”,不畏“宽仁之法”。导致当今反腐败“屡禁不止”甚至“越反越腐”的乱局正是这些“奸雄”造成的,是他们在“宽仁之法”的“伪法治”条件下(按:在传统法律观念中,“宽仁之法”等于“非法之法”,故相应的“法治”也就成“伪法治”了),毫无廉耻地无所不为、无所不取的结果。
面对政界、商界、学界“奸雄辈出”而一如战国“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般的乱局,中国思想界的“复儒”声浪日益高涨。在人才观上,其“复儒”者其实是要回归于以“儒法合一”、“以儒为主”为基本的思想特征的“宋明新儒学”——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人才观。
“复儒”者的用心固然良苦,其言也善,只可惜其言实非“劝世良言”,其策亦非“救国良药”,因哲学观念未能与时俱进,还是在传统本体论的框架内“筑梦”。
观当今时势,人类的竞争既不是“竞于道德”,也不是“争于气力”,甚至也不是传统意义的“逐于智谋”,而是在现代意义的“逐于智谋”。这是一个真正的并且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的“逐于智谋”的竞争时代!
在“逐于智谋”的时代,“智谋”是“人才”的实质所在,“道德”和“气力”只是人才的环境条件。对人才本身来说,“气力”是人才的先天性身体条件和后天性健康状态,“道德”是人才的认知水平、情感取向和意志状态——它们构成了人才的自我环境或内部环境。对国家来说,“气力”是国家的“硬实力”(包括先天性自然资源条件与环境状态和后天性物力、人力资源状况及其配置状态),“道德”是国家的“软实力”(包括群体性的信念、信仰和组织制度、组织行为规范等文化状态和文化发展水平)——它们构成了人才的社会环境或外部环境。这两种环境都只是人才的条件,而不是人才本身;其环境因素均属于人才的外因而非内因。把人才的外因当作人才的内因来理解,从而从“道德”和“气力”方面来界定“人才”,这是中国传统人才观的思想实质所在,是民智未开、知识未分时代由于智性尚未作为普遍的人性表现于人的个性之中所导致的。
随着知识分化的日益明显以至于以综合知识为特征的传统学术中逐渐分化出“科学”(“分科之学”),实验科学也应运而生。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实验科学蓬勃发展,“知识就是力量”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越来越成为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事实。到了后工业文明时代,实验科学更是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方向发展,以至于到今天已由“实证科学时代”转变成“信息化、数字化科学时代”。于是,曾经作为普遍的人性表现于人的个性之中的“道德”和“气力”,逐渐降至人性的次要方面,“智谋”则逐渐上升为人性的主要方面,从而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才观由原来的从“道德”和“气力”方面来界定“人才”,逐渐转变到从“智谋”来界定“人才”了,于是,传统的“霸道人才观”与“王道人才观”以及作为这两种人才观之综合形式的“德才兼备人才观”,也都逐渐降至处于次要地位的非主流人才观,代之而起的主流人才观是“智道人才观”。
“智道人才观”所崇尚的“智谋”有一历史发展过程:
农业文明时代的“智谋”是基于个人天赋和生活经验的“才识性智谋”——“聪明之智”。这个时代的人才概念是“才识型聪明人才”,此种人才类型以诸葛亮最为典型,故堪称“诸葛型人才”。
工业文明时代的“智谋”是基于实验科学的“实验性智谋”——“发明之智”。这个时代的人才概念是“实验型发明人才”,此种人才类型以爱迪生最为典型,故堪称“爱迪生型人才”。
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智谋”是基于科学信息化、数字化的“创造性智谋”——“灵明之智”。这个时代的人才概念是“创造型灵明人才”,此种人才类型以比尔.盖茨式最为典型,故堪称“盖茨型人才”。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继承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关系来看,农业文明时代的“才识型聪明人才”、工业文明时代的“实验型发明人才”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创造型灵明人才”,都是当今这个“逐于智谋”的竞争时代所需要的,对于处在这个时代的任何国家来说,这三种类型的人才都是缺一不可的,但是,任何国家想要使本国在异常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最终胜出,无疑主要不是依靠“才识型聪明人才”,而是主要靠“实验型发明人才”和“创造型灵明人才”,尤其要靠“创造型灵明人才”。
然而,在“逐于智谋”的时代,无论哪一种人才类型,其人才标准在本质上都不再是“有才”或“有德”抑或“德才兼备”,而是“有智”。这就是说,“才”和“德”对于人才都不再具有本质意义,而只有非本质意义了。非本质意义不等于没有意义,只是这种意义不具有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内因)意义,换言之,它只是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外因)。
根据“外因一定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辩证法原理,“才”和“德”作为非本质意义的人才因素一定要通过“智”才能起作用。这意味着,在“逐于智谋”的时代,“才”和“德”要成为人才的现实条件,必须与“智”相结合,而且在与“智”的互动关系中,“才”“德”只是起到促使“智”从可能的人才根据转变为现实的人才根据的助推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缺少,但它们本身并不直接构成为人才的要素,这种作用只是体现出它们是人才成为其人才的条件。如果它们不能促使“智”从可能的人才根据转变为现实的人才根据,它们连人才的条件都无从谈起。
因此,“逐于智谋”时代的人才培养,不再需要“智育”,因为“智”是人才的内因、根据,而培养人才的教育则不是创造人才的内因、根据,而是创造人才的外因、条件。而人才的外因、条件则不外乎“才”和“德”两个方面,故该时代的教育也无非是“才育”和“德育”两个方面。“才育”和“德育”皆应围绕“启智”来开展,要使“才育”和“德育”成为开发人的聪明之智、发明之智、灵明之智的手段,和成为保证聪明之智、发明之智、灵明之智从潜在之智转化为现实之智的条件。
在“逐于智谋”的时代,无论其具体要求类型如何,“智”都是作为普遍的人性,作为人的本质,而存在于每个人的个性之中,并且通过也只能通过其个性的充分张扬与发展才能来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该时代的教育(“才育”和“德育”)就是促使人的个性得以充分张扬和发展的过程,亦即为人的个性的充分张扬与发展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的过程。
“才育”的基本任务包括两个方面:(1)增强受教育者的体质,改善其健康状态和提高其健康水平;(2)发展国家的“硬实力”,改善国民的物质生活状态,提高其物质生活的质量与水平。
“德育”的基本任务也包括两个方面:(1)提高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正确引导其情感取向,磨练其意志而使之能自由选择和独立决定其行为。(2)发展国家的“软实力”,改善国民的文化生活状态,提高其文化生活质量与水平。
这意味着,在“逐于智谋”的时代,教育是国家的一种整体性行为,一个系统工程。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26&do=blog&id=5448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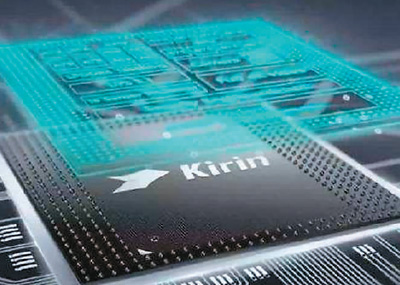
 001
001
 002
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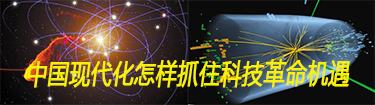 003
003
 004
004
 推荐席位
推荐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