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中国美国人民友好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名誉会长。曾任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2003年因倡导新一代可循环钢铁工业流程及建设环境友好型钢铁厂而被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2006年分别当选为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和俄罗斯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2008年当选为澳大利亚工程院外籍院士。1月26日,本报记者在中国工程院对徐匡迪院士进行了独家专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两个轮子
记者:徐院长,您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学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非常希望听到您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见解。
徐匡迪(以下简称“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活动的结晶。哲学与社会科学比起自然科学更为宏观、全面,如果说工程科技是解决一定领域内的具体问题,那哲学就是用来解决所有问题的。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工程院的定位是中国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当选的院士是其所在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
自然科学中的工程科技,与社会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在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下,工程院做过一个咨询大项目——三峡工程的后评估,即对当时的工程可行性报告、施工建设方案等进行再评估。这里面既有工程问题,也涉及社会学,比如移民问题;还涉及经济学,比如说三峡工程这么大规模的投资,前后十余年,不仅没有超预算,而且还略有结余。这是为什么呢?客观上,当时正逢亚洲金融危机,原材料价格降低了;主观上,资金运作比较好,财务和风险管理方面做的比较好。这就涉及经济学的话题,既有会计学、财务学的问题,也有宏观经济正确的预测、判断。我想工程院今后在咨询方面应该加强和社科院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作为一个工程科技工作者,我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已工作了五十多年,尽管后来到上海市政府工作,但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专业。在我担任市长之前,学校里的科研团队已经比较完整,我所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大部分都已从国外学成归来挑起了大梁,所以我可以利用周末及公余时间,让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起讨论科研问题,对于关键性的问题我也会到实验室去,要求学生将某些重要的实验重复做给我看。
进入政府工作之后,我多次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他们经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后来又从政,从事社会管理、行政管理工作,你觉得有什么转变?从深层次讲,这就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目前中国参与政府工作的,理工科出身的人比较多,这是五六十年代的教育结构造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需要大量的人搞工业化,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去学习相关专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经济建设是以抓大工程、抓大项目的方式来进行的。今后随着我国民主、法制的逐步完善,工业化、城镇化的全面推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要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等,所以将来一定会有更多学法律、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因此,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而不是某个个体有什么特别的。
记者:您从学术岗位转向领导岗位,就是当时国家建设使命所需吧?
徐:“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工作总需要有人来做,我本人没有什么特殊才能,只是希望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点贡献。不过,与现在的大学生相比,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有一个突出特点:社会责任意识更强一些。那时候大学生人数很少,国家对大学生寄予了很高期望,我们不用交学费,有饭吃,教科书也是国家发的。因此,自然而然地就有一种祖国培养我、我是祖国未来的骨干、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这和现在通过考试竞争入学的大学生有不一样的经济与社会背景。而且,我们念书时正值各种政治活动的频繁期,学生的组织能力也相应得到了锻炼。
从学科上来说,我认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特定问题、具体对象,很具体、很微观。比如,某一个器件上用的钢材,无论是在跨海大桥上用的钢缆,还是在矿井里用的钢缆,或是电梯用的钢缆,是不一样的,要适应特定的工作条件。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比较宏观,要求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来考虑问题。所以说,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更多哲学思维、辩证思维,自然科学研究则需要更多逻辑思维、线性推理及实验观察。
对于从事政府管理、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两者都需要。管理工作既需要有宏观的、整体的了解,比如说我们生活的城市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需要突破哪些瓶颈,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应主要抓哪些问题,这些是社会科学;但具体到选择何种技术,比如要解决市内交通,是选择地铁还是公交,或是地面轨道交通,这就是技术问题了,就需要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方法。比如,在设计上海的城市交通布局时,我们就采用了数学中的线性规划。
自然科学的好处是比较唯物的,但是有局限性。有时候在某一具体问题上是正确的,但如果不经慎重考虑就任意扩展其结论,那就很可能是悖论,甚至是反动的。比如纳粹将达尔文关于自然界生物进化过程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作为日耳曼民族优秀、进而要消灭其他“劣等民族”的理由,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另外,自然科学研究者缺乏宏观思维、辩证思维、哲学思维,也容易误入歧途。比如像牛顿这么伟大的科学家,发现了地心引力,推广到宇宙万有引力,天体在运动中因有引力而平衡,但是天体旋转的第一推力从何而来呢?最后,他认为只有“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上帝的信徒。包括爱因斯坦、DNA结构的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等到了晚年也都成了宗教的忠实信徒。
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两个轮子,少一个都不行。
社会科学应并重理论思维和实证方法
记者:您谈到的是一个很深的科学哲学问题。社会科学之所以被称为一种科学,是因为它符合一些基本的科学标准,人文与社科之分也是建立在这些标准之上的。请您谈谈怎样才能使社会科学更加科学,缩小它与自然科学发展间的距离?
徐:社会科学是研究时空跨度很大的、宏观的科学,它的基础是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思维方式的进步。社会科学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性,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实验,无数次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才能形成定理。不论是谁做这个实验,得出的结果应是一样的,才能称之为科学。如果只是个别人才有的偶然现象,没有通约性、没有重现性、没有实证性,就不能称之为科学。社会科学虽然是宏观的,但也需要社会实践来验证。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经过调查得出的,他环绕地球一周,观察了多种生物、标本,发现南美洲和大洋洲的生物不一样,他认为是适应环境、生存竞争、物种选择的结果。费孝通先生也借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亲自到很多村落去做调查。再比如考古学,得出任何结论都要拿出确凿的证据。近期关于曹操墓真伪有一些争议,主要就是围绕石碑是否为魏武王所有展开的,各家说法不一,这就表明实证是很重要的。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报》围绕曹操墓所做的特别报道就注意坚守以实证为基础的科学原则。
徐:对。不少社会科学也借鉴了自然科学中的数学表达形式和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比如在计量经济学中,数学的表达形式体现得就比较明显;在考古学中,利用碳14来断定文物的年代,借用了现代科学的手段;社会学同样需要做一些群体和案例的调查;即使是宗教学研究,也需要通过定量分析,研究历代朝圣者留下的遗物,以追溯到古代宗教的发源。
另外,我认为应从宏观上把握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我忠实信仰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的论断至今尚无人超越。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有一个总的科学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在正确的体系下才能有一些具体、可行的科学方法,如果连体系都不承认或作了错误的选择,那么社会科学的讨论就没有了基础,而不同范式下的辩论往往是无效的。
记者:您提到了科学的实证性,实证主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强调实践性,空谈理论的文章少了,具有实证性和现实关注的成果多了,但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现象,比如研究的碎片化,一些学者对宏观性、理论性问题缺乏思考,研究工作“匠气十足”;还有一些“唯方法论”式的研究成果,热衷于使用复杂的模型来得出一些近乎常识的结论。想请您谈谈如何处理宏观理论思维和具体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
徐:宏观理论思维是统帅,实证研究是具体手段。我刚才说的社会科学引入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等,都是在总的目标统领下所采取的手段。就像自然科学,也要先确定一个大的范式或大的系统、大的目标,然后再做具体的研究。如果抛弃了这些,研究就毫无意义了。如果费孝通先生只调查了一个农村就以它来代表中国农村的整体状况,那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自然科学中的“样本的有效性”问题,首先这个样本要具有代表性,要是有效的,才值得深入研究,才能定量化,才能再推广。如果样本已经偏离了大的系统,偏离了整个目标,那就没有代表性了,就会陷入琐碎、无效甚至庸俗的研究。
现实问题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应对
记者:提到气候变化问题,对这一问题,世界自然科学界是有争论的,当然,主流的科学家认为气候在变暖,但每当谈判进入到某些关键节点后,总有一些科学家站出来否定。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究竟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正常现象,还是另有原因?
徐: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都存有争议,100%的研究者都赞同的结论几乎没有。相对论、DNA的双螺旋模型等,都曾有人提出质疑。哥本哈根峰会前,爆出了一个“气候门”新闻,在东英吉利大学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PC)的电邮往来中,对一些数据是否确切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IPPC还误引了一个印度科学家的判断,认为2035年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将完全消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因为喜马拉雅山是“亚洲水塔”,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恒河等都发源于此。一旦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消失,对亚洲,尤其是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这个科学家并非无中生有,但是他只依据了最近几年的情况去推断未来,认为每年的变化速度都是差不多的,但实际情况是,山越高的地方越寒冷,积雪融化的速度就越慢,而且事实上喜马拉雅山区的雨雪量每年都有变化,因此,不能仅用新近有限的数据为依据。
关于气候变化,我认为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是很全面的。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本身是有周期性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冰河期,也有温暖期。自然界的气候波动和太阳黑子爆发、火山爆发、地壳内部运动等有很大的关系。最近200年来,气温是在升高的,最近100年来,气温升高得比较明显,而最近50年,尤其是最近20年的气候波动尤为突出,这和大量化石燃料燃烧释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有关。当然,对于受影响的程度、温度升高的幅度,科学界还有争论。
科学本身就是在争议中发展的,但不排除有部分国家的部分科学家是在为本国利益说话,比如,美国是最大的排放国,美国国内就有部分科学家认为,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小,而多数科学家及发展中国家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80%的温室气体是OECD国家在过去200年中排放的,这涉及排放的责任问题。科学家就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见解甚至争论,这是很正常的。但在关键时刻发出某种声音,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有政治背景,这里就涉及社会科学了。
记者:您曾是我国首位“院士市长”,后来又担任了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等职,也多次强调“院士是不退休的”。您是怎样协调好社会职务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的?
徐:承担政府行政、企业管理职务或研究院所的负责人,都是有任期的,不管是不是院士都要退下来。但院士不是行政职务,而是一种荣誉。院士在行政职务上可以退休,但为科学作贡献是终生的事,不能退休。社会科学家也一样,如季羡林先生近百岁高龄时还在研究中亚的语言文字、指导研究生;巴金先生100岁时还在写作;上海有位画家叫朱屺瞻,100多岁时还每天坚持作画;钟南山院士和我同岁,现在还在做呼吸道疾病的研究;上海的汤钊猷院士,已经81岁了,还在做肝癌方面的研究。对这些学者来讲,科学已经融入了他们的生命。社会职务和学术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人民、社会需要他服务,是社会责任;一个是自己挚爱的毕生事业。
学术期刊推动科学进步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阵地。在科学社会学领域中有一些关于科学共同体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期刊在促进学术发展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您能否谈谈如何通过期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徐:期刊作为学术交流平台,是推动科学研究进步的很好载体。如果有戏剧却没有剧院、没有舞台,那怎么演出呢?社科院的期刊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大平台,也是学术研究的载体,还是和国外同行进行交流的很好窗口。
办好一份社科期刊,平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很重要:一方面,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服务;另一方面,要鼓励学术自由,活跃学术气氛。不能误导读者与群众,如果只有一种思路、一种思想,尽管它非常正确、非常好,但时间久了可能对读者的吸引力会减少。不同的思想往往只有在争辩、碰撞中,才能撞出火花、辨别真伪。如何平衡好这两方面的关系,是办刊者的社会职责所在,也是对办刊者理论素养、学术水平的考验。我认为这对社会科学尤为重要,既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引导大家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贡献,又要“生旦净末丑”样样都有,增加可读性。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的期刊才能生动活泼,期刊才会办出味道来。
记者:现在社科领域的评价体系将在期刊发表论文作为一个重要因子,学者发表论文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在西方曾闹过一些丑闻,比如用一个软件可以造出假论文,所有的条件都具备,甚至可以发表。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徐:社会科学特别要防止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呢?虽然自然科学也有抄袭、也有剽窃,但很容易查出来,因为很多研究都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运用了数学和物理学的表达方式,要抄袭是很难的。然而,当我们讨论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政策时,只要在网上输入“宏观调控”,就会检索出很多篇文章,而多数研究者对形势的判断、给出的政策建议都大同小异。因此,这就很难判断究竟是否存在学术不端。
实际上,科学研究中要创新、要说不同的话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限定博士生、硕士生、专业人才评职称就必须要在SCI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未必是一个好办法。发表文章只是一个方面,关键要看他的研究有没有创新,有没有学术贡献。爱因斯坦发表的文章并不多,也并非发表在核心学术期刊上,而且他刚提出“相对论”的时候曾遭到过著名期刊的退稿,后来发表了还曾被若干权威物理学家驳斥,并多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所以说,不能将SCI作为衡量研究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如果不管什么学科、什么专业都用统一的量化指标去衡量,那显然是不合理的。
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导向很关键,要有一套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还要把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好。“文革”结束后,我们比较强调法治社会的建设,但社会不是单靠法律就能维系的,法律只能惩治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那剩下99.9%的人就要靠道德约束。因此,社会需要诚信和道德来维系。
办好一份社科期刊,平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很重要:一方面,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服务;另一方面,要鼓励学术自由,活跃学术气氛。
学术道德要从教育抓起
记者:您认为如何才能建立起这种道德的约束机制呢?
徐:要靠教育。现在我们社会的危险之一是引入竞争过早甚至过度,从而造成了道德教育的缺位。诚信教育、做一个诚实的人的教育必须从小抓起。小平同志在1989年曾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到目前为止,虽然教育不是最大的失误,但还是没有走到完全正确的道路上来。我们批判了过去的很多东西,想建立新的,却又没能建立起来。
如果抛开政治体系不谈,美国的教育体系在有些方面是值得借鉴的。比如,美国人的价值观教育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幼儿园的第一堂课是教孩子们美国的国名怎么说,画的第一幅图是美国国旗,不论画成什么样,反正要画52颗星、13道条,也要知道它们代表的是什么,同样,学的第一首歌就是美国的国歌。
这一点在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一个故事中,就有所体现。里根就任总统时,记者问他:“总统先生,您今天能成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我相信您一定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请问哪个阶段的教育对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影响最大?”记者的本意是想羞辱里根,因为里根既没有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又非名校毕业生,但里根的回答非常出色。他说,我所受的最好的教育,是我刚进幼儿园时,老师告诉我,当别的孩子摔倒的时候,你要把他扶起来,你要去安慰他,告诉他面对困难时不要害怕,要坚强;当你手中有一块饼的时候,你要看看周围有几个孩子,要把饼分给他们吃。我做总统就是要帮助那些在困难中的美国人站起来,勇敢面对生活,战胜一切困难,我要把美国的财富尽量平均地分给每个人。里根的回答成为了经典,虽然由于美国的社会制度他根本不可能兑现这一切,但至少说明幼儿园教育对他的影响的确很深。
希望《中国社会科学报》兼顾科普,传播真知
记者:最后还想请您为《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发展提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徐: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社会科学事业,社会科学期刊也好,社会科学报纸也好,除了发表学术文章以外,能不能也像我们自然科学搞科普那样,请一些名人和专家来深入浅出地介绍一些基本的社会科学知识。比如什么叫通胀、什么叫通缩、什么叫流动性过剩、什么叫杠杆率、什么是金融衍生工具、有哪些金融衍生工具,现在很多人都在用这些词,但未必知道确切的内涵是什么。现在电视上医药卫生类的科普做得就比较好,什么怎样养生啊、中医名医开讲啊,收视率还挺高。美国的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的科普做得也不错,还有刑事侦查类、考古发掘类的节目也都很好。邵飘萍很年轻就因办《京报》而成为大新闻家,并受到青年时代毛泽东同志的推崇,关键就是《京报》的“副刊”办得好,非常吸引人。我觉得,如果社会科学报能使没有系统学习过社会科学的读者也能了解到社会科学丰富的成果,就会很吸引人。
同时,办学术类报纸要能雅俗共赏。尽管学术性的解读与忽悠式的吆喝不同,但人们也可以很喜欢看。比如可以请考古专家介绍中国历代的玉器文化,请语言学家谈谈中国文字的演进,请宗教学者讲讲各个民族的宗教、原始宗教、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等等。现在一提到伊斯兰教,有些人就联想到恐怖主义,这是错误和片面的。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同时,要正确引导宗教信仰者和不信仰者,在相互理解与包容的基础上和谐共处,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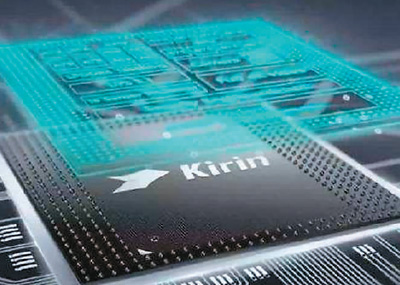
 001
001
 002
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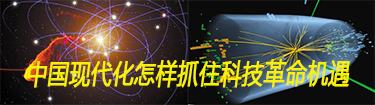 003
003
 004
004
 推荐席位
推荐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