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性主宰的生活世界
作者:陈蓉霞
2013年07月29日 来源:东方早报网
人类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容易忽略随机现象,我们总是执著地追寻原因,追寻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我们在杂乱无章的现象背后寻找到原因,就更容易驾驭现象,从而赢得生存优势。相反,当面对一个完全随机的现象时,我们就会陷入无所适从、无从决策的境地。
《醉汉的脚步——随机性如何主宰我们的生活》
[英]列纳德·蒙洛迪著
郭斯羽译
湖南科技出版社
2010年6月第一版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心理学家怎么会与经济学奖扯上呢?说起来,这与他早年的一段研究经历有关。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经为一群以色列空军飞行教官授课。卡尼曼强调,对正确行为进行奖励能起到矫正作用,而惩罚错误行为却没有同样效果。但一位学员却表示了不同看法,根据他的经验,当他因为飞行员做出漂亮的动作而表扬时,该飞行员下次的成绩反而会差;但当他因为飞行员糟糕的表现而责骂时,下次的飞行成绩却会提高。如此说来,惩罚比奖励似乎更有效,其他学员也认同这一看法。这就让卡尼曼陷入了沉思,因为根据动物实验,奖励有效,惩罚却是无效的。如何解释这一悖论?
卡尼曼给出的解释是,飞行技术的提高必须通过大量的练习过程,但在仅仅连着两次的飞行中却不可能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因此特别优秀或特别糟糕的成绩就只能归结为运气,但不可能每次都撞着大运,因此好运或坏运之后就是回归平常。结果似乎是,表扬无效,惩罚倒是有效。但背后的实质恰恰是,任何一系列随机事件中,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后面,总是更可能跟着一个相对平凡的事件,而这完全都出自偶然。用统计学的专门术语来说,这就是回归均值。
然而,为什么飞行教官却看不到这一点,而是将此现象归之于表扬无效、惩罚有效?其原因在于,人类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容易忽略随机现象,我们总是执著地追寻原因,追寻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我们在杂乱无章的现象背后寻找到原因,就更容易驾驭现象,从而赢得生存优势。相反,当面对一个完全随机的现象时,我们就会陷入无所适从、无从决策的境地。就飞行教官而言,当他们发现惩罚更能激励飞行员飞出好成绩时,至少他们会对自己的训练方式充满信心。
植根于人类思维深处的神学或科学同样表现出这种天性,亦即寻找模式并赋予其意义。神学的前身是神话,在各民族的神话中,一般都包含创世故事,亦即把自然界看作一位神的创造,比如汉民族传说中的女娲补天,尤其著名的当然是《圣经旧约》中的创世故事,神用语言无中生有地创造了整个世界。在此基础上,才有基督教神学,认定上帝不仅能够拯救人类的灵魂,而且上帝还是一位创世神,天与地都出自上帝意志。将宇宙归之于神的意志或设计,不仅令自然现象有规律可循,而且还为人类的出场铺垫意义。追溯至希腊哲学,柏拉图认为,世界起初混沌一片,正是神将秩序赋予宇宙。这些都意味着,人类偏爱一个有序的世界,混沌无序令人困惑乃至不安,甚至瓦解人生的意义。而偶然或随机性都与无序相关联,难怪我们不愿正视它们的存在。
就科学而言,尽管它不追问秩序的起源,但它却默认秩序的存在,并且以寻找秩序为己任。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宇宙之不可理解,就在于它居然是可以理解的。这里的理解显然就与某种秩序的存在有关。在此不由得想起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曼讲过的故事。他说,正是在父亲教他玩的游戏中,他知道了什么是科学。游戏的玩法是拼瓷砖,父亲教他在放瓷砖时一定得在一块白的后面接两块蓝的,依次重复,绝不能出错。渐渐地,费曼看出了门道,那就是图案的规则性。照父亲的说法,数学是什么,数学就是寻找图案。从那以后,费曼一生都在寻找自然界以各种方式呈现出的图案,从中寻找规律,同时寻找发现的乐趣。
但在《醉汉的脚步》一书中,作者列纳德·蒙洛迪却令读者正视一个事实:随机性或许在更大程度上主宰了自然界以及我们的生活世界。先从我们的一个常识性偏见说起。我们认定,有序只能出自于有序,或者说有序的背后受规律性的东西所控制,神创论即出自于此思路。但爱因斯坦对布朗运动的解释却颠覆了这一偏见。布朗运动是指微小颗粒在液体中的自发运动。但当时的经典物理学却难以解释这种运动何以产生,原因在于:首先,对于可见的颗粒来说,分子实在太小了,以致难以推动颗粒的移动;其次,分子的碰撞发生得远比观察到的颗粒的移动要频繁。但爱因斯坦的睿智就在于,他意识到这两种因素恰可相互抵消,亦即尽管碰撞发生得相当频繁,但由于分子如此之轻,以至大多数的碰撞都不可能产生观察上的效果,仅当某些时刻,当纯粹的运气使得某个方向上的撞击恰好互相叠加,以致它们的合力足以推动颗粒发生移动,这才会发生观察上可见的晃动。多么天才的洞见!经过计算,爱因斯坦发现,尽管存在着分子层面的混沌,但在分子的参数如大小、数量和速度等与可观察的颗粒晃动频率与幅度之间,却存在着可预测的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说其伟大,不只在于爱因斯坦合理地解释了布朗运动的发生机制,更在于,它首次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揭示,许多我们感知的自然界秩序(比如观察可见的布朗运动),在其背后,却是看不见的无序在起作用(比如分子的随机运动),这就意味着,有序可以源于无序,其机制就是统计规律在起作用。在分子的随机运动中,某个方向上形成合力尽管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因为分子数量的巨大,此种运气总能出现,并且在宏观层面上体现出来。
其实早在统计物理学出现之前,有序可以出自无序的观念已被天才的思想家所洞察。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市场体系的形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市场是一个可以自发调节的有序体系,但这种调节不是出自于有意规划,而是市场中无数个人随机行为的叠加,正如分子的随机运动,但其合力却造就一个有序的市场体系。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原理,同样是有序出自于无序的一个生动体现。个体出现变异性状是一个随机事件,但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之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结果就是适应性状脱颖而出,新物种随之形成,可见生物界的有序同样出自于一种盲目无序的竞争力量。不过在此值得强调的却是,达尔文当初心心念念想要做出的发现只是,在生物界中寻找类似于牛顿力学那样确定性的定律,用以解释一个谜中之谜——物种的起源。但事实上,达尔文于不经意间闯入的却是另外一个领域,其中占主导作用的不是确定性、必然性,而是随机性、偶然性。
将统计学运用于社会领域,就可以发现这一事实:尽管每一个人的行为具有随机偶然性,但群体行为却表现出某种规律性,比如死亡率或生育率等等,最早对此做系统研究的是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奎特雷,他的梦想同样是以牛顿为榜样,创造一门新的“社会物理学”。它要揭示的规律是,正如牛顿力学中一个物体在不受干扰时保持其运动状态一样,人类群体的行为在社会环境保持不变时,也同样保持恒定;正如受力情况下物体会偏离其直线路径一样,社会环境的改变同样会导致群体行为的改变。一个现实例子就是,“9·11”事件之后,人们出于恐惧而改为驾车出行,结果车祸丧生者要比前一年高出约一千名。如今在保险、销售等领域,已离不开统计学的运用。
随机事件,用日常语言来表述,就是运气。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都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对于个体来说,只是一种偶遇,最好是以平常心对待。但不得不承认,人生之命运却在很大程度上受此种偶遇所支配。不说别的,就说每一个人的出生,我们恰好得以来到这个世界上,难道不已经是一种天大的奇迹?就此而言,回溯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由一连串随机事件所铺就的轨迹。我们似乎面临无数种可能的人生历程,但最终我们却只能沿着一条轨迹展开,因此回顾过去,似乎只能用宿命论来解释。(顺便提及, 这种宿命论,若是体现在宇宙学中,就是人择原理,回溯过去,宇宙的每一步演化,似乎都在注定人类的出现。)然而,展望未来,由于运气之不可避免,结局就是未定、开放的。人生的精彩也就尽在这种不确定之中,因此人生不可能规划,也无需规划,随缘,甚至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或许就是一种生活智慧吧。
如此说来,要解释我们何以有今天之境遇,答案易求,因为轨迹已经确定,无关的变量可以被轻易地剔除,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学难以完全避免辉格式的解释;但若要预测未来之命运,则无从寻觅,不仅未来的变量处于变化当中,而且在谜底揭晓之前,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哪些变量可以被剔除,如此巨大的变量早已超出人们的可控范围。正如本书所举例,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似乎有不少蛛丝马迹暗示日军早有此预谋;但在事件发生之前,这些所谓的线索却很难被看作异常现象。正是这种解释与预测的不对称性,构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本质区别。比如就一枚炮弹的投掷而言,在初始条件确定的情况下,对其轨迹的解释或预测,其实是一回事。但若说算命先生真有可能根据某人生辰八字或星座之类,算准其未来命运,那顶多只是巧合或主观附会而已,可以为信,但不足为真。诚如本书作者所言,看清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会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解释和预言;我们可以更注重对事件做出反应的素质,如灵活性、信心、勇气与坚毅;而非依赖对事件发生的预测能力;我们可以更看重直接的第一印象,而非看重那些大肆张扬的当年之勇”。
深刻想来,宇宙或我们生活世界的背后,其实完全受随机、无序事件所控制,规律或有序只是局部小概率事件,但它对人类如此之重要,以致我们的大脑执著地要从无序混乱中寻找模式或是规律,并且赋予其意义。就世界的本来面目而言,这或许只是大脑所制造的幻觉而已。但这种幻觉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却是必不可少,因为当我们自以为能够控制我们的生活时,我们的焦虑感就会显著减小,显然这有益于身心健康。更进一步说来,生活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中,我们也会更加有安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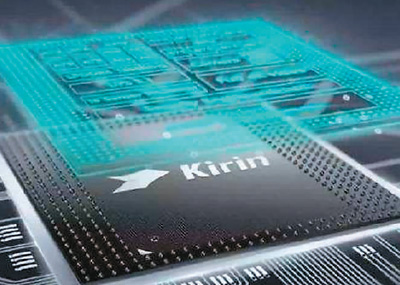
 001
001
 002
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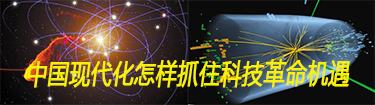 003
003
 004
004
 推荐席位
推荐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