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与造作
——论哲学在中国思想中重新开始的可能性
作者:丁耘
2013年05月22日 来源:
是否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是近十年前在中国学界引起热烈争辩的论题。这场讨论虽已沉寂多年,但由于缺乏一些前提性的反思,此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在根本上,这个问题既取决于对中国传统的思想的理解与谋划,也取决于如何看待“哲学”自身。在某种处境下,后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这或者是因为,在现代中国思想中,“哲学”及植根于它的整个学科体系以一种几乎勿远不届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体会与解释。如想避免对传统思想做出素朴与简单的最后解释,那么在理解传统之前,反思据以理解的整个框架与境域,应当是比较审慎稳妥的做法。换言之,在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思想”问题化之前,也应尝试着将“哲学”问题化。
哲学不是一个现成地摆在那里的标准。在大学兴起之后,某种变形了的亚里斯多德式哲学给出了一个清晰、完整而稳固的知识与教育体系。但在该体系的根基处,哲学的自我反省几乎从未停顿。从笛卡尔到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史都在不断贡献对哲学的不同解释。这些理解虽各有别,但作为同一个知识体系所孕育的自我理解,它们之间仍有可贯通之处。或者说,在西方哲学内部的显得差异极大的这些理解,一旦面对例如中国传统思想之类的他者,便会显示处其不言自明的一致性。这个事实提醒我们,一方面不存在一种凝固不变的哲学观,可作为硬性的标准来判决中国思想,另一方面,又要在西方哲学的自我理解中抽取出那个隐然为哲学划出界限的一致性。
这就要求我们,当在哲学思潮不断兴衰的历史中,找到那个通常据以判决中国思想的哲学观,并将之变成追问的对象。而捕获这个哲学观的先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尼采之后哲学史的主要贡献。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在其走得最远的地方,已经从自我解释推进为自我解构,并将这种解构当成哲学新生的主要道路。哲学的自我捍卫,在实质上也是回应这些拆毁的。如所周知,无论欧陆哲学还是英美哲学,哲学在拆毁时被刻画为“形而上学”或广义的“柏拉图主义”,在被捍卫时被刻画为“科学的哲学”、“政治的哲学”乃至“语言批判”。所有这些不同的指称都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传统的不同面相。
哲学必须追溯到苏格拉底一系,这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黑格尔与海德格尔都说过,哲学就是希腊的[1]。与这个提法相通,海德格尔也追随尼采说过,哲学就是柏拉图主义[2]。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曾给哲学下过一个谨慎的定义:“爱凝视真理”而真理则是“存在者(on 或einai)”或“一”[3]。亚里斯多德则正式将研究存在之为存在以及探索第一本体(ousia,或译为实体)立为第一哲学之根本任务。如此说来,海德格尔的说法似乎可以成立:哲学探索存在[4];而希腊哲学从起始直到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是为哲学之第一开端[5]。顺着这个思路,海德格尔在30年代之后标志转向的重要手稿中,将以自己接着尼采做的工作概括为:从哲学的第一开端过渡或者跳跃到另一开端[6]。到公开发表的总结性作品中,则又放弃哲学另一开端的说法,径直谈论哲学本身之终结与“思”之任务[7]。
就中国思想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而言,海德格尔的探索尤其值得重视,其间隐含着值得推敲的这样几层意思。
首先,如尼采之后的整个西方哲学的探索确具意义,那么就不可无反思地运用属于第一开端的甚或已终结的“哲学”(柏拉图主义、亚里斯多德式形而上学等)去强行解释甚至要求中国思想,相反要从这个传统的开端与终结的机理中回看中西思想的同异。
其次,哲学的另一开端或终结,绝非与哲学的第一开端毫不相干。恰恰相反,正如海德格尔的全部工作显示的那样,对哲学第一开端的透彻解释甚或激进解构才是通向另一开端的有效道路。开端意味着本源,只有彰显自身甚至比第一开端更为其本源,或以更原初的方式保持着本源,所谓另一“开端”才能成立。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对从前苏格拉底到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第一开端的检讨与阐发是尤其重要的。这非但决定他一生运思的成败,也彰显了发轫于尼采的整个二十世纪欧洲哲学的最终意义。
因此,第三,对中国思想的解释既然当以哲学之问题化为前提,则尤须关注在其开端与终结处的西方哲学。因为这是西方哲学自我问题化的极端时刻。这意味着必须清理到亚里斯多德集大成的古希腊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
本文试图即以哲学第一开端的破立所呈现的“哲学本身的问题化”为契机,进入对中国古典思想的重新解释。
亚里斯多德哲学中最显白、影响最深远的是其四因说及其背后的存在-真理学说。本文因此择取亚里斯多德哲学及其四因说为引导线索,首先以牟宗三为例,批判地考察以四因说为主干的哲学第一开端在解释中国思想时的效验与局限;其次以海德格尔为中心,批判地考察哲学第一开端在西方哲学终结时刻所遭遇的透彻解释及其致命的片面性;之后本文将通过重新阐发亚里斯多德哲学的整体经验之前提,判定哲学第一开端的历史意涵,并参之以《周易》、《中庸》为典范的儒家义理学;最后期待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哲学能否在中国古典思想的重新解释中找到新的开端。正如海德格尔隐秘手稿的标题所显示的,描述并且再次找到开端,这就是 “对哲学的奉献”[8]。
海德格尔本人对哲学之第一开端做了拓扑学式的多方描述。其中,在希腊文所谓physis 与德文所谓 Machenschaft之间进行对照,以表现出第一开端的内在张力与终结趋势,是比较重要的一种手法。Machenschaft包摄了希腊文 poiesis(制作、创制)与 techne(技艺)之中的存在领悟与解释,本文翻译为“造作”。Physis通译“自然”,但其本意为(植物的)生长[9]。海德格尔发挥此意,不以德文Natur,而以Aufgehen等译之,转为中文是为“涌现”等。在第一开端中,“造作”支配了存在领悟与解释,physis被“造作”褫夺了权力。而“对哲学的奉献”必定包含了这样的工作——逼问“造作”的本质,破除对physis的造作性解释,彰显其原意[10],跃向哲学之另一开端。本文以为,如先悬置一些微妙的差别——文末将回到这些差别上来——中文“生成”、“生生”等颇近于physis之原意。然则,对哲学开端之考量,以“生生与造作”为名,大略可以提示两个开端各自的源流及其间之摩荡往复。
一. 依四因说的新中国哲学及其局限——以牟宗三为中心
“哲学”并非中国思想本有的部类,“中国哲学”的成立是依“哲学”对中国思想的固有内容剪裁与解释的结果。这种解释首先依赖的是对西方哲学本身的理解。西方哲学之第一开端是以亚里斯多德为终结的。亚里斯多德及其所代表的第一开端对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一直未引起中国思想的哲学解释者们足够的重视。
亚里斯多德的幽灵不是那样容易被祛除的,他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抓住任何想依靠哲学本身的人。即使西方哲学所亏欠亚里斯多德的,也远比那些时髦人物所承认的要多。自麦金太尔之后,反省现代伦理前提的西方道德哲学自觉地从康德转回到亚里斯多德,以求回到古典思想的基本视野[11]。本文在自己的主题内,分析一个堪同麦金太尔的自觉性相对比的例子——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史叙述。
牟氏主要试图将康德的基本问题与概念运用到中国哲学的解释上:
“点出“性体”这一观念……故宋明儒所发展之儒家成德之教,一所以实现康德所规划之‘道德的形上学’,一所以收摄融化黑格尔之精神哲学也。”[12]
这段引文表明,宋明理学是康德道德形上学的推进,而黑格尔较之康德离理学稍远;也暗示了贯彻到底的康德式哲学可以涵摄黑格尔精神哲学——而这一切皆决定于牟对“性体”的哲学阐释与历史引导。
性体及心体固非西方哲学的概念,而牟氏处境已与乃师不同,故不得不借西方哲学名相以分疏之。按牟的论述,心性不一不二,“客观地言之曰性,主观地言心……性体本是‘即存有即活动者’,故能妙运用万物而起宇宙生化与道德创造之大用”[13]揭橥这於穆不已的性体实为《周易》、《中庸》之主旨。而《论语》、《孟子》则随诸发心点拨仁体,所重为心体。心体则是“即活动即存有”者[14]。
牟氏一方面以存有、活动这对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西方哲学概念化去了乃师熊十力的体用概念,以通释所谓心性之体,另一方面又说西方哲学中虽谈存有、本体[15]者甚夥,其实并无即存有即活动之性体概念,只康德之道德的形上学以道德进路切入本体界,大略近之。[16]
这一理路显示了雄伟的魄力与才具,同时也面临了一些困难。
说西方哲学除康德外,皆昧于“即存有即活动”之理,显然于史不合。即从近于康德之德国观念论谱系观之,费希特之“本原行动”、黑格尔之“主体与实体” 之统一,谢林推演之自然哲学系统,均较康德更近于“即存有即活动”之理。尤其黑格尔、谢林,已非从所谓“主观”的心体出发,而是从已被领会为“即存有即活动”的“性体”出发的。反倒是康德之道德形上学,大体只能说以心体通摄性体,绝无性体系统所必涵有之“本体-宇宙论”。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麻烦——
将康德哲学树为西学典范,以梳理宋明理学乃至先秦儒家义理学诸系统,最大的凿枘不合在于:从心体上通性体的康德哲学决计无法融摄《易》、《庸》,因而无法融摄明道一系的所谓“本体-宇宙-道德论”。盖康德之宇宙论属自然科学,全属于现象界。康德系统内唯一能突破此关的是目的论判断力学说,此则须以“假定”上帝存在为枢纽,与所谓关乎物自身的“智的直觉”无关。[17]。牟氏谓性体可起“宇宙生化与道德创造之大用”,此言至为谛当。然征诸《易》、《庸》,儒家义理学的性体是并起宇宙与道德之大用的,进路虽可有别,但割裂即非儒家。康德之病非但在于没有性体论上的宇宙生化,而只有心体论上的道德创造,更在于割裂本体-宇宙-道德论之统一。牟从康德入手通《易》、《庸》,正是所托非人,一生大误[18]。在《心体与性体》中,牟实际已点出了这个麻烦[19],但似未意识到这给他会通中西工作带来的致命困扰。然此究系典籍疏通上的障碍,最大的困难仍是义理架构上的,此即其用以儒家内部判教的“存有/活动”说。
在《心体与性体》中,牟完全依据这对概念会通中西、论衡儒学。然于此对概念的渊源,他却有意无意地不交代清楚。存有与活动这对概念的提出与深思,绝非始自德国观念论,而是源于哲学第一开端的完成者——亚里斯多德。《心体与性体》一系著作的麻烦在于,在对亚里斯多德这对概念运用到几近透支的同时,却对亚里斯多德全部思想的讨论轻描淡写,如不是漫不经心的话。
不过,在《四因说讲演录》这部篇幅虽短小、气象却更宏伟的讲义中,牟宗三通盘调整了义理架构与解释进路。存有/活动概念让位给了四因,康德式进路被亚里斯多德式进路所取代。亚里斯多德四因说不仅比存有/活动更好地疏通了《易》、《庸》系统,甚至可以在人类所有的中西五教系统之间进行判教,非徒限于儒家之内而已[20]。这样,在《心体与性体》写作二十余载之后,末年的牟宗三尝试了一个麦金太尔式的惊人转变,从康德转到了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为牟宗三带来了圆熟、宏阔与超迈,如果说《心体与性体》还只是限于宋明理学之内,借助明道学脉上通《易》、《庸》的话,那么《四因说讲演录》则出一头地,直接疏通《易》、《庸》,下摄宋明。
四因说、特别是其简化形态(质料因与形式因)在解释不同哲学基本倾向中可以说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第一开端传统下的西方哲学——以及仿照西方哲学进行的中国思想解释——可以说完全处于四因说的笼罩之下。例如,所谓“唯物主义”v.s“唯心主义”的史述论式即可追溯至对“质料因”和“形式因”的不同强调[21]。
然而,虽然“形式因”可以同“动力因”与“目的因”贯通,后两者仍然具有单纯“形式因”无法笼罩的深意。晚年牟宗三的一个极大贡献非但在于回到了亚里斯多德,更在于独具只眼,于四因中拣选动力因与目的因作为疏解儒家义理学的概念架构。在此,这两重原因起到了原先“存有/活动”概念的支架性作用。
牟宗三是从“目的因”进入四因说的。在从康德的道德神学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的推进中,作为“目的因”与“形上学”本身实际提出者的亚里斯多德就起到了较之康德更为关键的作用[22]。很明显,在康德、亚里斯多德与儒家义理学之间的交涉枢纽就是“目的因”。
牟宗三看到,中国古典思想虽无“目的因”及“动力因”的概念,却保有其意涵。整个《周易》的经传系统中最重要的乾坤两卦即分别含有这两层意思。乾卦代表始生、创生原则。乾卦的《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23]即揭示了这个原则。而坤卦代表终成、保合原则[24]。而《中庸》的“诚”则是贯通了乾坤、始终,作为“成为过程(becoming process)”贯穿了动力因与目的因[25]。
牟据此认为,儒家形上学是目的论的系统,且是中国古典思想中唯一的目的论系统[26]。唯儒家义理学是就宇宙万物总说目的因与动力因,而亚里斯多德除此层次外,还有就各事物分别说的目的因,而这也同事物之分别的形式因或形构之理相契[27]。牟通过亚里斯多德解决了康德哲学在疏通《易》、《庸》系统时的致命缺陷。《易》、《庸》与《论》、《孟》、《大学》取径有所不同,从天道下贯人道。正是目的因与动力因概念帮助达到了性体所涵的宇宙与道德之统一。
牟在以《易》、《庸》解释“四因”时,将动力因配“乾”,释为“始生”,将目的因配“坤”,释为“终成”。此既确切又颇具深意。盖“动力因”是经院哲学传统翻译arche时的释义(译为causa efficiens——效果因),此词字面意思就是“开始/本源”,而“目的因”(telos)字面确有“终结”之意。然而,细究牟氏对四因说的运用,仍可发现如下义有未安之处。
首先,亚里斯多德本人虽以目的之实现一致地贯穿在宇宙与道德两个领域中,但他既不像德国唯心论那样将道德所属的精神领域看得高于宇宙,也不像牟氏所解的《易》、《庸》传统中以天摄人,融贯天人。在亚里斯多德那里,伦理的事情低于宇宙和本体的事情。而伦理的成立,却又并不需要宇宙作为“天命之谓性”那样的保证,而只需要人类灵魂中较高贵部分的德性而已。这反而接近于“心体”,而不是与心体分离开的性体。这是牟的解释与亚里斯多德哲学最终意趣上的差别。
其次,亚里斯多德于四因中最重目的因。而牟宗三在处理儒家目的因与动力因关系时语多牴牾。他一方面判儒家为中国思想中唯一的目的因系统,另一方面追随宋明以来特别是熊十力的解释道路,渐将坤元从属甚至完全归并到乾元中去。也就是说,按照牟的自己的解释,《易》、《庸》系统是顺着康德、亚里斯多德一路推进下来的目的论系统,非此不能承担性体开出宇宙-道德之意蕴。然而按照牟进一步依靠的、以乾元为主的理学传统解释,则不得不将《易》、《庸》系统最后归入动力因系统。此系统其实是“即活动即存有”系统的变种,即将活动归于动力,将存有归于目的,且更为强调活动一面。
因而,牟宗三的所有会通性诠释工作包含了自我瓦解的趋势。他直接依据四因说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思想的伟大努力不可谓成功。除宋明理学以来对乾坤生成的安顿纠葛之外,牟运用四因说的最大问题在于未能做彻底的前提性反思。他似未能完全领会亚里斯多德四因说的整个前提与意图。特别是目的因为何在四因中最终占据主导,目的因在解决他关心的存有/活动问题(也就是心体/性体)中的枢纽作用。在亚里斯多德那里,目的因是对存有问题的最终回答,而动力因是对自然问题的最终回答,二者最终不一不异。这里首先应该检讨的其实是问题而非回答:西方哲学为何有“存有问题”,中国古典思想为何近乎提出了“自然问题”,却明显缺乏 “存有问题”。
这些才是哲学第一开端运用于解释中国思想之前必须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关于哲学的问题”。以牟宗三为代表的中国思想的现代解释者——也不妨称为新的中国哲学的建立者——于此类问题几乎全然是盲目的。在我们去亲身探索之前,考察一下西方哲学传统自身如何检讨成于亚里斯多德之手的第一开端,是很有助益的。
二. 破四因说的新西方哲学及其局限——以海德格尔为中心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对自身传统的周密检讨与自觉突破,首先体现在将自己的使命领会“解释西方哲学”的马丁.海德格尔那里。海德格尔一生运思围绕“存在问题”,且将之视为西方哲学的第一问题,遂依此立下解释全部哲学传统的基准。然而对哲学史稍有了解即可知道,存在问题并未在哲学诞生之初即出现。几乎全部前苏格拉底哲学都在研究“自然”问题。苏格拉底主要通过对伦理事物本质的追问来研究“善”,柏拉图亦顺之将“善”的理念视为“超越存在”的至高问题[28]。唯独亚里斯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明确将研究“存在之为存在”(to on hei on)作为第一哲学的最高任务[29]。因之,毫不奇怪,亚里斯多德在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上扮演了最重要的发动者角色[30]。
在“转向”前后,海德格尔对亚里斯多德的解读风格之间既有连贯性,也有断裂性。在后期,亚里斯多德本人逐渐成为解构的对象,海德格尔更加倚重前苏格拉底的哲学资源。他的工作更倾向于解构亚里斯多德及柏拉图传统加于前苏格拉底哲人的僵化理解。然而,正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悖论。一方面,他借以推进到前苏格拉底解释的那些基本概念指引——其中最重要的是真理与存在的多重含义——几乎完全是在前期的亚里斯多德解读那里阐发的。另一方面,海德格尔解释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全部出发点是——前苏格拉底哲学说的是“存在”问题,“自然”说的是“存在着性”(ousia)这个典型的亚里斯多德概念。这就是说,几乎不把 “存在”作为主题的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比亚里斯多德更本源地回应着这个亚里斯多德式的问题。
这个悖论的关键在于,从海德格尔被“存在”问题——或毋宁说“存在之(多重)意义问题”抓住的那刻起,就注定无法摆脱对亚里斯多德的依赖。亚里斯多德对存在问题的解决系统地依赖于他的四因说。在《形而上学》导论性的第一卷,他就把智慧界定为对“原因”的探索。在摆出“存在之为存在”主题的第四卷,他更将第一哲学的使命做实为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第一原因”。[31]通过第七、八、九诸卷的准备,他最终在第十二卷凭借拓展了的目的因学说解决了这个问题。与此对应,海德格尔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接过亚里斯多德的存在问题以及对“存在”与“存在者”概念的全部疏解,同时拒绝亚里斯多德以四因说解决存在问题。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四因的主导最终就是目的因,因此毫不奇怪,海德格尔对亚里斯多德解读中的实质性偏离是从削弱目的因开始的。
研究者们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对目的因的拆毁。舒曼(R.Schuermann)认为,海德格尔通过对亚里斯多德“技艺”(techne)学说的分析,将四因追溯到手工制作活动包涵的存在领悟,揭示了作为传统哲学源头的“手工业的形而上学”。他据此认为,海氏的工作是揭示并且拆毁西方哲学传统的“目的论统治”(Teleocracy),阐发了此在在其本真存在中的无所本(Anarchy)含育的一种新的思想态度[32]。此议不乏卓见,然而,舒曼认为海德格尔通过对亚里斯多德的解构,揭示理论/实践都是系统地植根于制作(poiesis)[33]。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沃尔皮(F.Volpi)在海德格尔对《尼各马科伦理学》的解读中发现的,支配海氏“此在分析论”基本框架的最重要解读指涉的是亚里斯多德的“明智”(Phronesis),而非制作概念。相比后者来说,前者更是亚里斯多德目的因学说之渊薮[34]。但沃尔皮的分析也有其弱点。其一,他的视野中缺乏《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借助其亚里斯多德解释试图展开的内容;其二,明智概念中包含的目的论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目的论,不同于作为存在问题之正面解决的目的因学说。对于“明智”这个伦理学概念究竟如何被“存在论化”的,他完全没有深入。其三,他没有认真对待海德格尔解释时发生的偏离。实际上,没有这种偏离,指向《存在与时间》甚至晚期学说的那种去目的论的“存在论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把海氏前期对伦理学的解释和后期对理论哲学的解释连贯起来处理,就能清晰地看到海德格尔是如何依靠、转用、偏离乃至遮破亚里斯多德四因说的。
海德格尔很少泛论四因整体。引人注目的例外是《论根据的本质》一文。在那里,他讨论了四因提出的先验条件。此文将一切“因”或“根据”的本质追溯到了此在之自身超越上。只有此在为其自身之故向着世界超逾,才有建立一切“根据”的“基本存在论”上的可能。而向着世界敞开与超逾就是“自由”,自由属于此在这种存在方式本身。“作为超越的自由……是一般根据的本源。自由乃是向着根据的自由。”[35]自由之建立根据的诸基本方式中包含了“论证”,或毋宁说包含了提出一切形态的“为什么”之可能。而在这种提问中已先行包含了对何所是、如何是以及存在一般之领悟。这就是说,没有此在之存在领悟,使得四因出现的那种追问是不可能出现的。正是此在之存在方式中包含着向某某追问。
这个“向着某某”问“为什么”的基本现象中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此在出离自身向外绽出的这个基本结构,这就是此在之自身超越或曰自由。另一是在这个绽出中需要的是“原因”或者“根据”。两下相合就是向着根据的自由。不过,按照《论根据的本质》中所推进的《存在与时间》中的思路,对于最终根据的“缘何而在”的追问势必会落实到此在自身,而此在自身这个如此亲近者也只有通过对茫然遐远者之追问[36]。不过,此在自身的基本存在方式又是出离自身。海德格尔据此总结说,自由固然是诸根据之根据。但作为出离,自由又是此在之“深渊”(Abgrund,字面意即“取消根据”)[37]。
看起来,海德格尔是将四因作为派生的东西吸纳到此在之求根据的自身超越中去了。但将此文放到海德格尔对亚里斯多德的解释整体中看,就会发现情况并不如此简单。正如沃尔皮等揭示的,此在之存在方式本来就基于对亚里斯多德“明智”的存在论式转译。而明智自身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又应当通过目的因及动力因加以确切的认识。这样看,海德格尔对四因整体的吸纳与消解其实是以对四因各自的具体转用为前提的。
可以在其他文本中看到海德格尔对四因的不同处理。对于形式和质料这对原因,正如舒曼等强调的,源于海德格尔对制作与技艺的现象学解释。在亚里斯多德比较钟爱的那些例子里,一方面自然物与技艺产品的区别并不妨碍他在自然与技艺之间的高度类比[38],另一方面具体存在物经常被比喻成技艺的制品。海氏据此在对“制作”(Herstellen)的现象学分析中,将形式、质料追溯到了制作的条件上[39]。注意,在这个主要讨论技艺-“制作”的场合,他并未涉及动力因与目的因。
海德格尔对动力因与目的因的探讨,则不得不更为复杂,既包含伦理学中的解读,也有形而上学上的相应解析。这是因为,亚里斯多德在伦理学中提出的实践、行动以及技艺,最终是在形而上学中以潜能/实现这对概念加以描述和认识的。这对概念本身,其实就是动力因/目的因的更深刻形态。在《形而上学》专论“潜能与实现”学说的第九卷,亚里斯多德将动变范围内的潜能概念分为两类,一是受作用,另一就是动力因意义上的潜能[40]。而“实现(energeia)就是目的”[41]实现作为潜能发为事功(ergon),其完成就是“隐德来希”(entelecheia),后者字面直译就是“达到目的”或“达到终点”。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实现在“定义”、“时间”尤其是“本体”三个方面均先于“潜能”。换言之,目的先于动力。动力是对目的之“趋向”,是为目的而在的。动力虽是“开始”,目的才是真正的开端。顺着这一思路,《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用其“实现”学说解决了此书追寻第一本体的中心任务。
不惟宁是,亚里斯多德同样以“潜能/实现”学说解决了描述实践这一与伦理学对应的问题。作为动变渊源的潜能亦存于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42]之内。与无逻各斯的潜能不同,该动力潜能可以造成对反的效果,两个对反只能发生一个,决定这点的不是动力潜能,而是“欲求或者选择”[43]。而“每种实践或者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44]“每种欲求【也】少不了某种目的。”[45]非常清楚,是目的或者某种善决定了有逻各斯的潜能之实现。考虑到善与目的在初次提出四因说的语境下曾被当作同义语使用[46],似可确定,在亚里斯多德那里,目的因是实践之主导原因。
然而,海德格尔在解读亚里斯多德以上学说时,做了关键的偏转,削弱乃至颠覆了亚里斯多德赋予目的因的主导地位。
在对《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疏解中,海德格尔极为重视第六卷中对灵魂把握真之五种方式——也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谓五种“理智德性”的讨论[47]。这五种方式非但包含了知识、努斯以及智慧,也包含了明智(实践智慧)与技艺。海据此发挥出了此在“存在于真(理)之中”[48]的观点,并且获得了区分不同意义之真理与存在方式的起点。照沃尔皮的看法,海氏特别注重技艺与明智的区别,这一区别对应着《存在与时间》中非本真与本真两重存在方式[49]。明智概念的存在论化就是在《存在与时间》中起了突出作用的“此在”概念。
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技艺的目的是产品,而技艺的始因(即动力因)则在技艺主体也就是人的灵魂之内。或者说,技艺活动本身不是技艺的目的,而技艺的目的因与动力因是有差别的。明智的目的则并非某个具体的产品,而是要“对一种好生活在总体上有益”,而“实践的始因(动力因)就是实践的目的”[50]。海德格尔正是抓住了明智的这类特点加以发挥说,明智的对象就是此在自身[51]。“目的与明智具有相同的存在特性。”[52]这就是说,实践的目的既非某个具体的活动,亦非活动的效果或事功。为了颠覆通常对明智目的之理解,他强调说:明智中所思索的是人生整体,“而非实践在那里达到终限(Ende)的东西……对行动之在来说构成性的不是结果,而只是如何(Wie)。”[53]针对亚里斯多德当作实践目的提出来的“做得好”或“活得好”(希腊文为eu),海德格尔转释说,目的既然是“好”,那就是“如何”,而非某个“什么”、某个特定的世内存在者。
在这里可以发现海德格尔对亚里斯多德精微的偏离。他首先像后者所批评的那样,把“好”脱离了“好东西”或“好事情”[54],变成一种不附于任何世内存在者上的“如何。”这也是海氏区分存在者方式之差异乃至存在论差异的意涵之一。其次,生命是“如何在”,是一种不同于任何作为 “何所是”的世内存在者的、我们一向所是那种存在者。这样一来,在“善好”被转为“如何在”的同时,“善”与“此在”乃至“生存”就开始了混同。明智的对象既然是生命自身,那么生命自身又是没有着落的绽出,那么善好作为“如何在”就无法落脚于任何目的,而只能成为一种殊特的存在方式。把“善”转为某种“存在”方式,这不是为了从存在出发去解决善的问题(就像亚里斯多德对柏拉图所做的转化那样),而是为了让“存在问题”完全排挤掉善的问题。这,才是在“存在论”层面对目的因所做的根本性的消解。
如果说在对伦理学的解释中,海氏还顺着亚里斯多德的文本,将实践的目的等同于实践的动力因的话,那么,在对《形而上学》第九卷的解释中,他就明确把目的因吸纳到动力因中去了。在那里,他将在伦理学解释那里获得的东西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个目的作为“如何”其实是归属于动力(Kraft)的[55]。而这个作为动变渊源(或翻译为始因、动力因)的潜能之本质中“仿佛包含了这样一个自在的要求:超克自身(sich zu uebertreffen)。”[56]
动力,作为开端,起始,当然是通过离开自己才成就为自己的。但如将海氏对于《形而上学》同《尼各马科伦理学》的解释合勘,不难发现,后者中作为明智对象的此在自身,实践的“主体”,就是《形而上学》第九卷中的具有逻各斯的潜能。此在对作为目的的善的关系,就是潜能与决定实现的、所选择的善的关系。从中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以自身超越为存在机制的此在,源于动力因的存在论化。这个基本机制,在海德格尔学说内部,固应归诸时间性时间化之“绽出”结构。但在哲学史渊源上,与其像沃尔皮那样归诸“明智之存在论化”,不如更透彻地交还给明智中所包含的实践动力因。或者说,存在论化了的明智正是作为动力因的有逻各斯的潜能。明智所与之相同的此在这个存在方式正是一切动因(开端)所蕴涵的自身超越机制。
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动力因在一般情形下确然只是开端,而非终极。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表述,它仅仅是“绽出”,而没有达成。用牟宗三发挥的周易术语讲,这个动因也仅仅是“生”,而不是“成”。但是,必须立刻指出,亚里斯多德绝不曾用动力因吞没目的因。凡是在他指出目的因与动力因合一的场合,都是目的因起着动力因的作用,而非前者被后者吸纳不彰。用他钟爱的自然事例说,果实既是生长的目的,也是作为生长过程开端的种子之所从出的真正的开端。这就是实现先于潜能[57]。换言之,终点(目的因)先于开端(动力因),而成为开端的开端,绝对的动因。宇宙生化与实践行事之目的-始因同一,不过如是而已。
那么,海德格尔是怎么看的呢?“作为果实,植物返回到它的种子里……任何一种生物随着其生长也已开始走向死亡,而且反过来讲,这种走向死亡也还是一种生长,因为只有生物才能走向死亡;其实,走向死亡可能是生命的最高行为。”[58]相反,亚里斯多德认为,达到目的(完成、完善)这个意义上的终结是善的,必须和作为转语的终结也就是死亡区别开来。目的不是结束,不是死亡。目的必然包含善。[59]要之,在亚里斯多德那里,不可能像海德格尔那样读出潜能、死亡与匮乏的优先性。
由此可引出一个辩证的结论:海德格尔对四因的破斥恰恰依赖于他对四因之一的动力因之转化。从对伦理学的具体解读中看,海氏是把对人生整体的考虑夸大为明智的唯一对象,而将对世内事务的谋划全都打发给技艺。换言之,正是因为在伦理学中牺牲了亚里斯多德实践概念包含“涉世性”在内的两重性,他才能在存在论上消除目的因,从而把动力因单独提炼为此在之自身超越的绽出机制。
这里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局面,对于亚里斯多德四因说,无论像牟宗三那样发挥,还是像海德格尔那样破斥,他们最终竟不谋而合地全都强调动力因、淡化目的因。差别仅仅在于,牟氏是受《易》、《庸》的理学解释传统的诱导不自觉地走到了这一步,而海氏完全是别有深意的。
但这样一来,依赖亚里斯多德来重释中国思想,与超克亚里斯多德来重建西方哲学,却落到同一窠臼里去了。无论依赖还是超克,全都缺乏他们自认的彻底性。为此,不得不重新回到四因说的起源,看看被两位二十世纪哲人有意无意忽视的目的因学说究竟何以得到亚里斯多德本人那么高的重视。
三. 生成、造作与哲学的第一开端——四因说的起源与密意
对亚里斯多德而言,四因说不仅是他个人的贡献,更是哲学本身所要求的。因而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在四因说的内部打转[60]。这样说来,对于本文的基本任务——将哲学本身问题化——而言,没有比考察四因说的起源与深意更妥当的进路了。讯问哲学第一开端的前提,也就是讯问四因说及其所蕴问题意识之所从出的原初经验整体。
原因(aitia)概念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里就已出现,这对于确认理念论的起源有决定性的帮助[61]。但柏拉图并未整理出一个系统的原因学说。把原因确立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概念,这是亚里斯多德的贡献。
亚里斯多德曾在两处地方郑重地提出四因说,一处是《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三章[62],另一处是《物理学》第二卷第七章。这两处的学说都是引导性的。没有它们,第一哲学与物理学的主干研究无从展开。从文脉看,前者关涉哲学一般,而后者关涉自然研究这个分支。所以不妨先就前者来考察。
在《形而上学》之首卷首章,亚里斯多德就把智慧与经验特别是技艺区别开来。与经验相比,技艺包含了对于原因的知识,因此更富于智慧。但无外在实用目的的理论知识比制作-技艺知识包含了更彻底的对于本源与原因的认识。因此“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本源与原因的知识”[63]。顺着这个结论,亚里斯多德明确地将哲学的任务确定为探究原因。在首卷第三章,他系统地提出了“本体意即何所是”、“质料或基底(主词)”、“运动之始因” 及其相反者意即运动之“终极与本善”这四类原因。而早在前一章,亚里斯多德已经说明了,理论中的最高门类在于认识目的——即事物各自的“本善”与全自然的 “至善”。[64]
可以看到,四因是在智慧与技艺的差别中被引入的。但这不是亚里斯多德就此差别所做的唯一发明。在某些方面更为系统和丰富的讨论见于《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六卷。在那里,智慧与技艺的首要差别并不是对原因的认识的彻底性与纯粹性,而在于,智慧是理观性的,关注的是永恒的、必然的、普遍的、不变的主题。这些主题高于人类的实践与器物。而技艺则是制作性的。它和明智一样,关涉的是暂时的、或然的、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类事物。[65]作为知识和努斯的统一,智慧所观照的崇高主题包括自然。这样一来,《形而上学》开篇引导出四因说的“智慧之超迈”,就被《伦理学》落实为例如自然物对制作物的超迈。而自然与技艺的差别正是《物理学》第二卷引导出四因说的基本进路。《伦理学》第六卷在四因说的两个出处那里架起了桥梁。如我们所见,这桥梁的中心是在三处文本里共同出现的概念——“技艺”。正是通过同技艺及制作不断区别开来,智慧与智慧所研究的自然才显示了重大与崇高。这就是说,技艺对于四因说似乎具有某种亲缘关系。
不过,这些亚里斯多德式的清晰在其根基处却带有某种不可测的含混。
首先是对技艺的限定。亚里斯多德在对技艺单独进行讨论的时候,没有忽略,除了“制作”之外,技艺中还包含了“使用”。制作技艺需要认识产物之质料,而使用技艺则要认识制作产物之形式[66]。更有甚者,他暗示了使用技艺是主宰或统治着制作技艺的“主导性技艺”。[67]此类内在区分明显和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做出的区分相通[68]。由于柏拉图没有明确区别技艺与实践,他以使用技艺来解释的东西恰是亚里斯多德倾向于用实践或明智来解释的[69]。
然而,当亚里斯多德试图用技艺与自然或实践、智慧等进行对照时,他就默默地将之限制为制作技艺[70]。正是这个限制支持着《物理学》的开端,乃至渗透到整个四因说的前提中去。
正如《形而上学》的开篇,亚里斯多德必须把智慧与技艺区别开来以引导出四因说那样,《物理学》第二卷一开始,他也通过把自然与技艺区别开来,以证成对自然的四因式探究。自然与技艺的区别首先是“万有论”上的区别。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有的是“由于自然”而存在,有的则是作为技艺的制作产物而存在。正如亚里斯多德不止一次指出的[71],希腊文“自然”(physis)的原意是生、生长,其后意义拓展为向着结果的生长也就是生成[72]。作为所生成者,自然物与被造作出来的技艺产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始因在自身[73],而后者的根源在自身之外——“人由人产生,而床却不是由床产生”[74]。这就是说,自然物与制作物的主要区别在于动力因是否归属自身(是否由“自”而“然”)。
不过,动力因归属的提出,仅限于将自然物与制作物区别开来。动力因既非唯一的、亦非首要的发问方向。整个《物理学》第二卷的唯一任务在于揭示全部四因 ——特别是目的因——适用于自然研究。为此,在把自然物与技艺产物区别开来之后,亚里斯多德立刻反其道行之,在自然与技艺之间恢复了一系列决定性的类比,以便在自然研究中可以按照形式、质料特别是目的去发问。
亚里斯多德首先区别了自然与自然物。自然相当于自然物之原因。自然物“按照自然”运动。而自然与自然物的关系,类似于技艺与制作物的关系[75]。自然物具有质料与动因是明显的,亚里斯多德最需要论证的只是,自然物也有形式与目的。此时他不得不乞灵于自然与技艺的相似性。“如果技艺模仿自然,并且,在技艺中认识形式与质料是同一门知识的任务,那么……自然学也就该通晓形式与质料这两种意义上的自然。”[76]“如果按照技术的东西有目的,那么显然,按照自然的东西也就有目的。”[77]
要之,四因说能够用于自然研究的理由在于:自然与技艺类似(这个类似是由于技艺模仿自然);制作技艺具足四因;自然物因而具足四因。自然在最高的意义上,等同于自然物之“目的”与“形式”[78]。然而,在《形而上学》、《物理学》以及《伦理学》的引导性教诲中可以发现,对包括自然研究在内的智慧全部说明都在于先同技艺划清界限。据此矛盾,似可轻而易举地像海德格尔那样解构亚里斯多德[79],或干脆像舒曼那样宣布,亚里斯多德实际上暗自依据“手工业”的造作经验缔造了全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
从海德格尔等的批判可以看到,哲学第一开端的关键在于技艺与四因之关系。是否像亚里斯多德的上述诸篇引论显示的那样,四因源于造作经验的先行领会,而又施之于自然之生成问题?是否四因说的秘密就在于把自然也比拟为某种制作产物?
从表面看起来,由于在解决第一本体问题中占据很大比重[80]因而流传最远的两个原因(形式与质料)确实同制作技艺有密切的关系。但亚里斯多德本人在四因中最重视的是目的因,而标志着亚氏哲学特点、将他同例如柏拉图区别开来的则是形式因、目的因与动力因的合一。换言之,形式因最终被整合到目的因中去,因而整个形式/质料这组原因全都被潜能/实现这对被目的因主导的概念重新赋予了含义。这样,要彻底了解上述问题,就得将之推进为,主导着四因的目的因是否源于技艺经验抑或其它经验?
无疑,在《物理学》第二卷中,亚里斯多德确实借助与技艺的类比确认了,自然物同样具有目的。然而,技艺的目的究系何指呢?对此,《物理学》中蕴含着两种不同的回答。按照第二卷第八章的论述,技艺的目的就是制作活动在那里终结的东西,也就是制作产物[81]。另一方面,在同卷第二章,亚里斯多德同样在讨论技艺的语境下指出:“我们所用的东西,全都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自己就是目的。”[82]据此,技艺的目的乃至一切“目的”被精细地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制作活动所指向的(towards which),即产物;一种则是制作活动所为的(for which),即使用该产物的人[83]。后者虽是使用技艺的直接目的,但同样也是制作技艺的最后目的。制作的产物不是别的,正是被使用的东西。制作是按照使用的需要去形塑质料的。亚里斯多德随同柏拉图重新确认,使用技艺“主导着”制作技艺[84]。考虑到柏拉图有意将“技艺”的范围扩充到足以包含实践的地步[85],似可确认,与被亚里斯多德限制为“制作”的狭义“技艺”概念相比,以人为目的之“使用技艺”更接近于“实践”概念。“使用技艺”对“制作技艺”的主导,意味着“实践”对“技艺”的主导。
实践对技艺的主导,对于彻底勘察四因说的前提,进而重估作为哲学第一开端的亚氏形而上学来说,是极为关键的。本文不能同意被舒曼所激进化了的海德格尔式结论——四因说乃至整个形而上学均出自“造作经验”中包含的先行领会。我们的理由是,在《物理学》与《形而上学》关于宇宙的最终方案中,亚里斯多德论证了,自然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是合一的。而在制作技艺那里,动力因与目的因则是明显不同一的。亚里斯多德诚然借助了与技艺的类比来引出自然之目的,但这一类比不足以引出自然的目的就是自然之动因。不惟宁是,亚里斯多德把实践与制作技艺明确区别开来的论断正是:“实践的始因与目的是相同的”[86]。不存在自足的制作。实践主宰着制作。手工业制作总是嵌在实践的语境中的,谁如果试图像舒曼那样宣布有所谓“手工业的形而上学”,那么他一定已不自觉地随之引入了“实践的形而上学”。
那么,标志着亚里斯多德哲学最基本特征的“动力因与目的因之合一”确实来自“实践经验”吗?事情当然不会那么表面。核诸亚氏在各著中的多方论证,似可确认,亚里斯多德不是简单地诉诸“实践”,而是更重视“实践”本身的条件。对实践条件的分析,与对自然运动和理论沉思的分析殊途同归地揭示了“动力因与目的因之合一”。换言之,既非单纯的技艺,亦非单纯的实践,而是实践、自然与理论所共有的原因状况才是亚氏目的论的真正精髓。这个东西就是亚里斯多德用他的哲学史概括预先表述的东西——心(努斯)与善的关系。亚里斯多德强调说,心就是动力因,善就是目的因。善又不离其它形式而在,而非超然于其他理念-形式之上的终极。这样就把三重原因的思考,与他先前的重要哲人联系起来了。实践、自然与理论沉思的最终的原因分析,都是以心与善的关系为哲学-历史的引导的。
阿那克萨哥拉提出了“心”(努斯),但却仅将之理解为动力因[87]。苏格拉底-柏拉图看到,单纯的努斯只能解释宇宙产生,却无法解释宇宙为何以这个样子存在,换言之无法解释宇宙的秩序及其善好。由此,他们把讨论推进到,努斯必须按照善来决定选择什么秩序安排宇宙[88]。按照四因说的术语,为弥补动力因的不足,柏拉图提出了目的因(善)和形式因(理念)以解决宇宙秩序的起源。但在这里,动因虽是为了善好、按照理念行事,三重原因却是有分别的。善与理及心可以分离,且超越于后两者之上[89]。柏拉图的神只是一个动力因,善高于它。没有理念,神亦无法成事[90]。柏拉图的创世论,四因具足而彼此分离,完全符合“制作技艺”的特点。亚里斯多德则不然。其宇宙-本体-神论最后的模式固然也是宇宙因神而动,但亚氏的神不是单独的动力因,而是目的、动力、形式三因合一。
三因合一的论证,在实质上就是宇宙-本体-神论不同论证道路的殊途同归。《物理学》与《形而上学》的旨归完全一致,无非一从动因、另一从目的因以及形式因揭示而已。亚氏在前著中从动因出发,将自然描述为“自己治愈自己的医生”[91]。而在《形而上学》中,他则从目的因出发宣布,“其实健康自己才是医生”[92]。
但是,这个宇宙-本体-神论的归宿,最后赅摄三因的第一本体或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经过亚里斯多德拓展的“努斯”概念。阿那克萨哥拉那里的努斯只是单纯的动力因,以至于苏格拉底必须为它补上“善”这个目的因。亚里斯多德既将动力因与目的因合一,则称之为善或心,都无不可。但心这个名词,在亚氏之前的哲学史上已经出现了它的动词形态——“思想”或“心思”[93],已为亚氏准备好了讨论心的“存有与活动”的概念基础。因之亚里斯多德主要用“心”及其动词化(“思”)支撑起《形而上学》里最崇高的那些段落
“心思(noesis,或译为“思”)本身是关于那至善,至高无上者关于那至高无上者……心触及所思、把握所思,心与所思相同。凡能受致所思与本体(ousia)的,才是心。当心秉有所思时,它才是实现活动,故与其说心容受神性,不如说心秉有神性。所以理观(theoria)是至乐至善……并且生命也是属于神的。生命是心之实现活动,而神就是一种实现活动,神的实现活动自在地是至善的与永恒的生命。因之,我们说神就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存在者,以致生命、连续不已之永恒均归属于神。这就是神。”[94]
“因此如以心为至善,心就只能思神圣的自身,【则这种思】就是思思之思”[95]
这两个段落可说是整个亚里斯多德哲学的顶峰。此间关涉的是对全部西方哲学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一为心之自足性。其二为心与神的关系(因而蕴涵着哲学与神学以及宗教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也是彼此互为表里的。其三是神的存有之永恒性包摄了连续不已之永恒性。
在亚里斯多德那里,三因合一的最彻底论证是从神(即善)之实现性与心之自足性出发的。前者是目的因下摄动力因。后者是动力因而上通目的因。前者类性体摄心体,后者近心体通性体。心之自足性的成立,端赖于作为心之活动的思想的特性。心贯穿天人。人灵魂中最高贵的部分是其本心。此心之高贵,端在于可参与宇宙之大心、神心、道心。《论灵魂》中对人心之思的考察结论,也适用于其所分享的、《形而上学》中关注的宇宙大心之神思。在《论灵魂》中,亚里斯多德以心之所思(noema)与心(nous)为同一,或以心之所思与行思(noesis)为同一。亚氏认为,心与所思只在所思之当下一念才是同一的。无思无虑之时,心似白板,与所思只能为潜在地同一。而行思与所思在均是无质料之形式(eidos)的意义上合一。并且当前一念只是潜在地可分,在现实性上是不可分单统一者[96]。
在《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第九章中,这几个观点都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再现。只是,那里的主题是作为宇宙之始因的大心。大心及其行思、所思为一,就是之神及其思、所思合一。这样一来,宇宙之本,就是思想自身的思想。神,不外于心或者思。因此哲学思维是最神圣最虔敬的。这就严格论证了上文所引之段落。什么是神?心及其思就是神。心何故自足?心之存有不外乎其活动亦即思。而心之能思与所思现实地合一。
神、心、思三者,本无分别。唯因如此,宇宙方有其永恒运动,周行不殆。
此观点虽是西方哲学史上被概括为本体-神-论的大传统,但亦因此概括,易生误解,须加说明。
柏拉图在一般理式之上高悬“一”或“善”这两个分离的超越理式,将此喻为日光,无之则心对理式的思想并不可能。从根本上说,正因善之理与心分离,柏拉图宇宙论才是制作模式。亚氏则以为,当前一念的思想,就是现实上的“一”。此单一体只在潜在意义上可分割为多。则所谓“一”,不离形式而在。除形式外无所谓孤立之“一”[97]。而柏拉图在日喻中归诸分离的“善”的“显明照亮”功用,亚氏亦归诸努斯之当下实现的思想[98]。然则所谓“善”,亦不离心及形式而在。由此可见,亚里斯多德将“一”与“善”融摄于心-思之中。以心思吸纳理式,不立分离之一与善,这才是自足学说的精义。唯此才能真正了结所谓“手工业的形而上学”。
唯因无分离超越之“善”或“一”,故虽不无斟酌犹疑之处,然亚里斯多德的神最终不外于心-思而在。故说形而上学为“神学”在字面上固然并无不确。然而亚里斯多德的神与柏拉图-奥古斯丁-笛卡尔-斯宾诺莎一系超越于“心-思”的神大异其趣,反而与宋明理学中某种天心合一的传统有可通之处。
由以上分疏可知:亚里斯多德四因说的起源不单限于始因终因有别的造作经验,而更多地体现在自然生成与实践智慧皆有的、始终二因合一的自足活动。而四因说之密意在于,无论体现为自然生成还是实践智慧,自足活动之精义要在于心之思虑,无论是神心还是人心之思。因此,亚里斯多德之自足学说,衡之以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义理学,可算某个形态的心性论。
四. 结语:造作、生成与生生
至此,我们终获得一个基准,用以权衡二十世纪中西哲学各自的重建,并进而探究哲学另一开端之可能。
海德格尔以“造作”解哲学第一开端,盖有所见而未澈。亚里斯多德对柏拉图的推进、以及海德格尔本人的亚里斯多德解释表明,“造作”必隐含了“实践”。而实践中包含的动力因(生)与目的因(成)之对待及其解决才是哲学第一开端之主导问题。换言之,实践之理是“生成”的统一性,即与动力因合一的目的因之自足性。追究“造作”,当推至追究“生成”及其自足性。
海德格尔之破四因说,本意在以动力因破目的因,进而拆毁自足学说。立动力因之超逾性,则有赖于遮破亚氏时间学说之当前性,以引出时间性之“绽出”。而当前性实系于思想形式之实现。故海氏工作之要害在于破实现、自足这些属于目的因及形式因的部分。由于遮破目的因,海德格尔之“此在”只有“生”之机,而终无“成”之理。由于遮破形式因,其存在一般终是笼统虚寂,只一个昭然明觉,而绝无万物自得、各安其位之理。由于遮破自足,此在与此存在一般,只是一个悬问、空等,亚氏之幸福终被茫然之“畏”取代。就存在问题本身看,存在者并不仅存在而已,且必定作为某物存在。而一旦探讨此物的内容,亚里斯多德式的目的、形式诸因并生成活动,必重新涌入哲学。西方哲学欲绕过亚里斯多德重新开端,除非消除“存在”问题。然囿于传统与语言,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揆诸海德格尔的所有思想努力,跳离哲学之第一开端,无非就是从亚里斯多德之“存在”返回前苏格拉底之physis。其中蕴含了至少这样一条道路:以一种去存在中心的心性论重释physis经验。然则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消除存在追问之至上地位后,心性论可否仍以某种形态开展与转化?在“生成”-“造作” 传统之后的physis之经验,可否哲学之另一开端?这就是中国哲学重新开端的发动性问题。它涉及两个环节,分述如次。
(一)去存在中心的心性论
问题之前一环节可确然答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所有心性论内容,都不是围绕存在问题建立,但又包摄了存有之理。中国心性论之伟大传统与西方哲学的会通交涉,是现代中国哲学建立的最重要契机。牟宗三的亚里斯多德阐释,实已契入此机。牟之宏伟努力有不可通之处,亦有可转进的方面。举其大者,不出以下两端。
其一曰混同体用论与存有论。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最明显的差别在于不把系词转为义理问题,因之以存有/活动褫夺体用论架构,极易失却中国思想之真面目。体用论渊源有自,绝非西方哲学之逻各斯传统所能笼罩。中国思想如自身可取,恰恰在于以体用论融摄存有论,而非反其道而行。
其二曰不解四因说之旨归与理学正统有大异。亚氏恰恰以四因说——而非存有/活动——论证了心体性体不二。其枢机在于自足。自足性之建立,在于心思不二、神心不二。后者即心性天三者无别之意,前者即蕴所谓“即活动即存有”之意。然亚氏所重,素在目的因,于《周易》只当得坤元。而整个宋明儒学是合释乾元诚体而立。于理学看,亚里斯多德哲学固亦近乎心性论,然却是以乾属坤之心性论。且其于心,只见用,未见体。其用只有思虑,未有感通也。
然而牟氏之努力,毕竟极值得推进。其最大贡献在于将亚里斯多德哲学引至儒家义理学视野内。重建哲学必始于重解亚里斯多德哲学,中西概莫能外。儒家义理学完全可以自己的传统解开、重构亚氏哲学,并进而回到儒家义理学的传统,开辟哲学的新道路。此则与上述中国哲学重新开端问题之第二环节有关。此间的工作,即参照亚氏“生成的心性论”之经验与理据,回看与重释中国古典思想。
(二)从生成到生生
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七卷规定,第一哲学的任务是探究“何为存在亦即何为本体”[99]。于第十二卷则总结云,本体可分为三类:可感觉而永恒动变者,可感觉而可坏灭者,不可感觉而永恒者[100]。此本体分类交错了动静、可感不可感、永恒灭坏这三重标准。《物理学》将永恒动变之原理确认为自身不动之致动者,《形而上学》则之间研究不可感而永恒者。而后者在《形而上学》结论性的一卷之被引入,实因借助“实现”原理解释永恒动变[101]。而此使宇宙永恒运动之第一本体,正是宇宙之神-心。
这是亚里斯多德理论哲学中最主要的进路。这一进路意蕴有三,首先,在《物理学》到《形而上学》的理论哲学的大构架中,动静之标准起着首要作用。其次,运动者也是存在者,也是某类本体,不动而致动者则是第一本体,使运动自身存在之更优先的存在。换言之,动静标准,最终转为存在的优先性问题。最后,寂然不动而又使万物动者,唯心体而已。可据此将亚氏第一哲学概括为,以存在-本体问题所引导的、旨归为心性论的生成学说。
从这三层意蕴看,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真正努力,即从永恒运动(其范例为永恒的圆周运动[102])推演出作为第一本体的不动心体。而以《易》、《庸》为典据的儒家义理学,亦无非从永恒的循环运动(反复其道、周行不殆),立寂然不动之心体性体而已。其明显的差别在于没有提出源于系词的存在问题。然而此问题所蕴之深意,则不可谓在中国思想中毫无端倪。
亚氏哲学是生成论进路的心性论。动力因即生,目的因即成。此进路有两个麻烦需要解决:
其一是一切生成论都会遇到的麻烦,生与成为二元(在中国思想中这叫“二本”)。亚氏之学是二元归为一本,亦即动力因归为目的因,生归为成。他的麻烦在于,二元合一不彻底,而合一在目的因,又有混同心意、将未发归于已发之弊。
亚里斯多德之四因中,形-质与生-成俱为二本。亚里斯多德虽将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三者合一,仍与质料因对待为二本。但从第一哲学最重要的论证看,动力、目的之对峙显然同样致命。亚里斯多德对二本的克服是以目的因发动力因之用,合二本为一。目的因与动力因合一,是为心体。心之所思不外于心,是以作为动力因之心,与作为目的因之所思相同。然而这一论断的最重要根据,仍在于所思是无质料的形式[103]。因此质料与心之对峙,仍未消除,不得不纳入于潜能/实现之下。此对概念所共属一体,却仍是动力因/目的因对立的变形。
西方哲学传统中解决二元对立的努力,主要依靠亚里斯多德的基本洞见,以目的因吸纳动力因,无非论证两者合一的方式不同。唯尼采之后学,多反其道行之,把动力因从目的因之下解放出来。用理学论太极的话头说,动力因只是个发生之理,目的因只是个成性之理[104]。第一传统下的西方哲学向来重视成性,而海德格尔等则重视发生——海氏哲学转向的代表作不就是《论发生》(Ereignis)吗?在亚里斯多德哲学的最微妙之处,生成关系无非是心与所思之关系,是以第一个麻烦势必引向关于心的麻烦。
其二,亚里斯多德以宇宙之始因为自身不动的推动者。而此推动者即是心。那么问题是,心动否?心之思是否心之动?如心不动如枯槁,则无所谓思,亦无所谓自然生化。如心以思为动,则所思当是所动,致动与所动不可为一,则心与所思何能合一?此问题于亚氏哲学必不可解,因他将动静看得过窄,似只看做“可感界” 的有潜能-质料之事。在物理运动与技艺生成中,潜能与质料含义可通,而未思之心(某种意义上的未发之中)虽不含质料,却纯是潜能,如同白板。[105]如在此意义上理解宇宙之大心之体,就会产生“永恒运动的原理是潜能”之谬。这就必须引入本心(choristheis【nous】)、习心(pathetikos nous)之分别[106]。前者决非白板似的潜能,而是思之整全的纯粹实现;是一念全观:既非对部分与片断之思维,亦非念念迁移之思维过程,而是不在时间之中(换言之处于永恒的当下之中)的体物而不遗之纯粹活动。
如是,宇宙之大心虽不能以物理运动言,但却是纯粹活动,不仅是“不被推动”那么简单。以动静论大心,须不落非此即彼之两边。对此,实际上埃利亚学派有其卓见。克塞诺芬尼以为神无外部,故不动,而以“思想”让世内事物运动[107]。此论与亚里斯多德实同。而巴门尼德继而据“能被思的与能存在的是同一的” 将存在者比喻为自身之内运动的圆球。[108]“在自身中运动”极好地阐述了心之思想的特性——即是运动,又不出其位,是思想自身的思想。这个比喻唯一的缺憾是暗示在这种自身运动之外可以有某种持存的东西。顺着埃利亚派的说法,亚里斯多德的心思其实就是在自身中运动。除了这自身运动,它自身什么都不是。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牟宗三所谓“即活动即存有”之心体与“即存有即活动”之性体合一之西学渊源——只是这个活动,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就是思。思之外本无心,活动之外本无存有。在思那里所体现的自足生成,就是生之当下顿成。生与成的二元对峙的最终解决,是借助心与思之关系,了然自成者无非是生,即生即成。但这一点,是从亚里斯多德论神心之思那里提炼出来的。他的宇宙论仍然是目的作为不动者先行存在,引发宇宙之永恒运动,最终仍落入存有先于活动、成先于生的进路。亚氏成立第一哲学的基本问题绝绕不开“存在”(是)或“本体”,即是所成先于能生之意。目的论的渊薮就在“存在”之中,海德格尔欲去目的而问存在,岂可得乎。
从根本上说,所谓哲学之第一开端,无非是在存在-本体问题的引导下建立成先于生、同于生的体系。而由海氏自觉开启的第二开端,则径行颠倒,在存有问题的引导下描述先于成、不居于成之发生(Ereignis)。在中国思想遭遇海德格尔并籍之重新发现亚里斯多德及整个西方古典思想之后,从中国思想由以兴起的整全原初经验重新审视、权衡哲学开端的机缘已经成熟。动静、生成、天人、心、神、善、甚至形、质等等希腊哲学问题域的若干地标式概念,在中国古典思想中非但一应具足,更同其他一些名相一起,构成了儒家义理学的宏伟脉络与深邃意趣。亚里斯多德所总结的希腊哲学,有两条问题线索,其一是《物理学》中的运动,其二是《形而上学》中的存在。彼终将运动归摄于存在之下。正因存在必须融摄且解释永恒运动,故有自足实现、隐德来希之本体解说。以《周易》、《中庸》代表的儒家义理学,固非由存在问题所引导,但确乎同样以不息不殆之永恒运动为经验上的基本问题线索,且将存有(是)之意摄入运动原理之下[109]。如果说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精义是存在性(本体)概念统治下的活动原理,那么儒家义理学的精义则是去存在概念的活动原理。这就是儒家阐释的生成-生生之道——易或诚。
儒家义理学之经验境域自限于天地之内。而于天地之间,更重天道。先秦儒家有法天、知天、事天之教[110]。宋儒更针对儒佛分际云:“圣人本天,释氏本心”[111]。天之为天,在于其不殆不息不已的“永恒”运动。此于儒家原典中毕露无遗。《周易》“乾”卦之《象》曰“天行健”,孔颖达《周易正义》云,“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复”卦之《彖》云“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故《周易》所谓“行健”,字义相当于《老子》所谓“周行而不殆”[112]。《中庸》则云诚者,天之道也。而至诚不息,是亦以不息描述天行,而以至诚阐释天道。这与《物理学》拿来做出发点的“永恒运动”本无二致。于《易》、《老》等强调周行、反复相同,亚里斯多德认为运动之首为位移,而位移之永恒者为体现在天体运行中的圆周运动。圆周运动是永恒的[113]。
不过,永恒运动只是共通现象,其道、理为何,才是义理学之秘要。中国思想的贯通,是从同将永恒运动确立为首要现象线索开始的。而中西思想的分野,则始于对永恒运动的不同解释。在亚里斯多德之前,几乎所有希腊哲人,都把生灭动变等作为意见追溯到其后的某些永恒存在物。亚里斯多德也正为探求永恒运动之道,才通过范畴学将运动分类,更凭借四因说提出了纯粹实现——即作为第一本体的心。如果可这算作从名理入手的“逻各斯道路”,那么儒家义理学则走着一条直面运动与事物本身,直接描述运动本身之呈现的“现象学道路”。在《周易》系统中,天地是乾坤的“形”、“象”、“用”,而乾坤就是范围天地的“元”、“体”。这两个“元”不是任何存在者,而是某种“方式”(就是海德格尔偏爱的那个Wie),是径就其“德”所获之名[114]。“乾,健也。坤,顺也。”[115]乾就是“健”,坤就是“顺”,一音之转。按照《周易》的这种指示方式[116],无论主词还是显明意义上的“存在”无非也是某种“德”。或可表现为“贞成”或“大有”,但无论如何不可算“元”,低于乾坤。
照《周易》系统,永恒生成运动之理,正是作为天地之道的乾坤。乾卦六爻皆阳,却有保合太和之用,通天地之共德,蕴“一阴一阳之谓道”之精义。虽然如此,二元一本的紧张在经学解释传统中仍然存在。为避免将天道与一阴一阳之道混同,应当确立将阴阳、乾坤、天地之德的张力均体现于其中的“一本”概念。在儒家义理学的历史上,符合这个条件的概念不止一种,且彼此有思想史上的联系。在《周易》系统中,它就是“易”;在《中庸》系统中,它就是“诚”。由“诚”之解释开出的宋明理学史上,它也可以是“仁”、“心”、“性”等。
无论《乾凿度》之“至诚”,或《春秋繁露》之“中和”,皆已提示了《周易》与《中庸》之间的隐秘联络。而将《易》、《庸》之间的线索明朗精密起来,且示来者轨辙的,当属宋明理学之祖周敦颐。其《通书》的阐释进路,即以《周易》的乾卦之德去解释《中庸》的“诚”。
“诚”既完全解决了二元一本的麻烦,又把“易”系统的主要问题——动静以及天人——全部接收了过来。可以说,“诚”的系统是“易”的系统的阐释性转化。
《易传》非常明白二元一道之内在张力与偏至。故《繋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117]。虞翻注曰“谓乾能统天生物,坤合乾性,养化成之。”李道平疏曰,“仁者偏于阳,见阳之息谓之仁,故仁者观道,谓道为仁。知者偏于阴,见阴之藏谓之知。故知者观道,谓道为知也。”[118]是仁者偏于乾之生,知者偏于坤之成。皆非一道之全体。《繋辞》紧接着就感叹说:“故君子之道鲜矣”。仁知之偏,皆因从乾坤阴阳一元理会道体之全。仁者主始生,即重动力因。知者主终成,即重目的因。以此回看亚里斯多德的目的因系统,是知者之学无疑。
二元一道既有偏颇,其解决之途有二,
或张大乾元,以纳坤德,以一道系于乾元之下。此即李道平所谓“一阴一阳,皆统于乾元。”[119]
或单提诚体,统摄乾坤。此即《中庸》之所以作。经过宋明理学在《易》、《庸》之间反复的发明推阐,清季易学家从《易》这方面已非常清楚,向前跨一步就是《中庸》。李道平在对“继善成性”章注疏的结论部分说“乾各正性命为‘性’……人得乾善之统,资坤之化以成性,故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即《中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也。”[120] 是《中庸》首句,即从张大之乾德来。乾德即天命。其变化正性,是以其“利贞”之德,通摄坤元。故“天命之谓性”,一统乾坤、生成之语也。《中庸》纲领落在一个“诚”字上,盖“诚”即张大之乾元也。此即周敦颐《通书》之精义。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21]没有其它什么词句比这更明朗地显示了天人之际,既全部保留了《周易》法天之旨,又比《周易》更为直接地将天人关系凝结在一个字眼里。《中庸》用《周易》自己的道理揭示了《周易》的前提——天地成位源于法天之诚。
诚与乾坤是一类概念。它也同健、顺一样,是一个从德目里借用的概念。从人德里借用的概念能指示天道吗?这引起了坚执价值/事实界限的哲学史家们的疑问[122],好像希腊哲学从未用善、心、思、言、统这些同样源于人类现象的概念解释自然本源似的。“诚”之殊胜绝不亚“思”、“言”之属。《说文》将“诚”“信”互训[123]。则“诚”即是所言成就,是意或者话实现了自己(诚意、修辞立其诚)。用西方哲学的方式考察,“诚”中当然凝结了思维、语言、存在、真理这些头等的哲学意蕴。用中文义理学的名相考察,它纳入自身之内的最重要意蕴就是“生”和“成”。就字面而言,“诚”即指所生之言意实现、达成——生而必成,即是诚。
就《中庸》而言,“诚”与“成”的字面上的密切关联是很容易发现的。就《易》、《庸》之内在关系而言,则“诚”将乾“生”、坤“成”之德合于一体,与张大之乾元相通,彻底解决了二元一道的难题。
从《中庸》的文本上看,诚比乾元更鲜明地强调了终成之德,且将其发扬光大、贯穿始终。“诚者自成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124]
此句当与《繋辞》“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合勘。《易》《庸》均不主有偏。然《易》则以乾仁属始生,坤智属终成。其道在始终之贯,其偏在始或在终。毕竟以乾始摄坤终、以生摄成。而《庸》之道则在内外之合。其偏在内或在外。据其文气,则成物之知更属不易。《易》大“继善”,而《庸》重“成性”。后者在《易》的系统中属坤之终成。《繋辞上》又云,“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李道平以为即上文“成之者性”之意。“存”,据《周易正义》“谓保其终也。”[125]“存存”与“生生”同,不已之貌。唯生据始言,存据终言而已。《易》将生存、生成分于乾坤始终。而《庸》则以诚一贯之。这非但回应了《易》系统的始终问题,且回应了《庸》系统自身的内外问题。强调并光大终成,并将之转进为“成物”。是诚将坤德创造性地转化并收入自身之明证。
另一方面,《庸》更主乾元“不息”之德,圣人“不已”之德,且将天人之乾德均绾合于“诚”。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126]
这是《中庸》的关键段落。其与《周易》有所异同,极堪玩味。《易.坤》之《彖》云“坤厚载物”、“德合无疆”[127]。则《庸》所谓“博厚载物”、“悠久无疆”,显出于《易》之坤元。“大明始终”[128]之“高明”则属乾元。周家之《易》,繋乾于首。故曰乾“首出庶物”[129],“天尊地卑,乾坤定矣”[130]。《庸》此章却极重坤元之德。先“无疆”之“悠久”、“载物”之“博厚”,而后才是“高明覆物之天”。看似颠倒了《周易》的乾坤天地之序。
然而,《庸》繋之于首的既非悠久亦非博厚,而是 “至诚不息”。《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31],《庸》则引《诗》云“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132]不息不已,显属乾元之天德。于是可知《中庸》分辨不息之天与高明之天。不息不已之天就是“至诚”。不息之天以其悠久“成物”,高明之天“覆物”。成物于前,覆物于后。如无成物,地载个甚么,天又覆个甚么?所谓“无疆”,《易》将之配坤。《庸》则单提之配悠久,直通于不息之天,转入乾元。《易》之“无疆”属坤元,盖指地大无疆,即“直方大”之“大”。[133]《庸》转之通于 “不息”之天,盖指贞下起元、生生不息,则转疆域之“大”为古今之“久”矣。而《庸》又未失《易》坤元之无疆义。《庸》云地之道“生物不测”,“不测”即坤元“广生”之意耳。唯《庸》将“无疆”之述脱离坤元,其用转宏。盖《周易》终卦为“未济”。《序卦传》释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无穷”即“无疆”。则《中庸》之意,盖以乾元不息之天德,贯通《周易》始终,而别名之曰“诚”。
《周易》生生不息之意,体现于“物”之无穷。“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134],则天地非物,而是万物无穷之理。万物无穷之理,即诚之不已不贰、易之生生不息。体用不二,易、诚、天、地之德,又必现于万物无穷、君子不已,而非悬于人物之外之存有。无论《易》、《庸》,皆主成性存存、反复其道之意。始生必有所终成,而终成又非绝对目的,必更始起新。此与中国思想不可以“存在”(是、所是、本质等)问题为主导,是同一思想事件的不同面相。中国古典思想之精义,在于以生生摄生成。单提生成,只是元亨利贞。生生不息,则蕴贞下起元、一阳来复。如是,无论释之以易或诚,不息不已、悠久无疆,才是physis大化流行之全体大用。哲学之另一开端,由此而现。
[1] “‘哲学’本质上就是希腊的。”,参见,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载,《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上册,页591
[2] “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参见海德格尔,《哲学之终结与思之任务》,载Heidegger,Zur Sache des Denkens,Max Niemeyer Verlag,Tuebingen,S61、63
[3]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第五卷,475e4,476-480。参见Platonis Opera,Burnet本,第四卷。并Plato,Completed Works,ed by J.M.Cooper,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pp1102-1107。版本下同。
[4] 参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3节。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页12
[5] “伟大的东西从伟大开端…..希腊哲学就是如此,它以亚里斯多德为伟大的终结。”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译,商务印书馆,1996,页17;关于“第一开端”,参见下一条脚注。
[6]参见Heidegger,GA 65,VK,FAM,2003,SS176-180。此稿名为Beitrae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哲学文-献》。一译《哲学论稿》。
[7] 参见Heidegger,Zur Sache des Denkens,Max Niemeyer Verlag,Tuebingen,S61
[8] Beitraege zur Philosophie的字面意思是“向哲学的奉献”或“哲学文集”。
[9] 参见《形而上学》第五卷第四章,并《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末
[10] 特别参见,Heidegger,GA 65,SS126-128
[11] 参见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08
[12]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上册,页34
[13] 同上,页36
[14] 参见同上
[15]牟以“存有”翻译 being,,以“本体”翻译substance。
[16]牟宗三,前揭 页33、34
[17] 可特别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第84-87节。康德在那里对自然神学与道德神学的分辨,当然不利于进入《易》、《庸》系统而言。中译本可见《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
[18]劳思光先生尝力诋《易》、《庸》混淆事实与价值。虽非儒门可接受,然其理路倒正是新康德主义余韵。欲依康德而辟劳氏,岂可得乎?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民书局,2004,第二册,第一章,陆之三,柒之四。
[19] 例如他一方面明确区别《易》、《庸》与《论》、《孟》,谓前者是本体-宇宙-道德论的系统,一方面又在西学对应之宇宙论系统中列了亚里斯多德与怀特海。参见同上书,页31-35。
[20]参见牟宗三,《四因说讲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225
[21] 这当然不是“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发明的。从康德开始,德国唯心论自己的哲学叙述与哲学史清理本来就在这对概念中兜圈子。马克思主义是针对德国唯心论的用语进行颠倒的。但颠倒改变的只是这对概念之间的权重,而非这对概念本身,更不是检讨这对概念的共同起源。
[22] 参见《四因说讲演录》,页16
[23] 《周易正义.乾.彖》,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0,下同。
[24] 参见,牟宗三,同上,页17f。牟宗三甚至建议把“目的因”改译为“终成因”。
[25] 参见同上,页18
[26] 参见同上,页16。这是对照道家与佛家所下之断语。
[27] 参见同上,页39
[28]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509b6-10。
[29] 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1003a21,除特别说明外,《形而上学》中译据Aristoteles’Metaphysik,Neubearbeitung der Uebesetzung von H.Bonitz,Felix Meiner,Hamburg,1989希德对照版译出。
[30] 参见W.Brogan,”the Place of Aristot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idegger’s Phenomenology ”,in Reading Heidegger from the Start :Essays in His Earliest Thought, ed By T.Kisiel and J.van Bure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4, P213
[31] 参见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1003a30
[32] 参见R.Schuermann, Heidegger on Being and Acting:From Principles to Anarch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ton,1990之第二部分,特别地是13、14节
[33] 参见同上,P255
[34] 参见F.Volpi “Being and Time:a ‘Translation ’of the Nicomachean Ethics?” in Reading Heidegger from the Start :Essays in His Earliest Thought, ed By T.Kisiel and J.van Bure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4,,PP200-205
[35] 参见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页191f
[36] 参见同上,页204
[37] 同上,页202
[38] 参见亚里斯多德《物理学》第二卷第八章。原文参见Aristotle’s Physics, W.D.Ross校注导论本,Oxford,1998。英译可参见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ed by J.Barnes, Princeton 。University,1995,Volume One, pp339-341
[39] 参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页138-145
[40] 参见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九卷第一章。
[41] 同上,第九卷,1050a9
[42] 参见《形而上学》第九卷之第二、五章。又见《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一卷第十三章。本文所引版本为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ed by J.Barnes, Princeton 。University,1995,Volume Two , p1729-1867。灵魂之“有逻各斯的部分”及其与其它部分的关系才是实践与德性之渊薮。
[43] 《形而上学》,同上,1048a9-10
[44] 亚里斯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一卷,1094a3-4
[45] 亚里斯多德,《论灵魂》,第三卷章十,432b15。本文所引版本为Aristoteles ,Ueber die Seele, Mit Einleitung,Uebersetzung(nach W.Theiler)und Kommentar herausgegeben von Horst Seidl, Felix Meiner,Hamburg,1995, 希德对照版。
[46] 参见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章三,983a31
[47] 参见亚里斯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六卷;并Heidegger,GA 19,Platon:Sophistes,VK,FaM,1992,第4节到第9节
[48] 参见Heidegger,GA 19,Platon:Sophistes,VK,FaM,S23
[49] 参见 F.Volpi ,前揭,P202f
[50] 《尼各马科伦理学》1140b15
[51] 参见,Heidegger,GA19, S48
[52] 同上,S49
[53] 同上,51
[54] 参见《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一卷第六章亚里斯多德对分离的善的理念之批评。
[55]Heidegger,GA 33,Aristoteles,Metapysik,?1-3 ,1981,S99
[56] 同上,S101
[57] 参见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十二卷,1072b35-1073a
[58] 海德格尔,《路标》,页347f
[59] 参见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五卷章16,1021b25-31
[60] 参见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三-第六章。又《物理学》第二卷章二,194a30-35
[61] 参见,柏拉图《菲多》,例如99d。Hackforth,R. plato’s phaedo translated,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 Cambridge ,1955
[62] 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二章,亚里斯多德重新回到了四因说,其内容与《物理学》第二卷第七章基本相同,但在这里没有像后者那样发挥了对全书讨论的引导作用。
[63] 《形而上学》982a。而按照第五卷第一章的讨论,“本源”这个概念可以被吸纳到“原因”概念中去。于是,早期希腊哲学探讨的“本源”都是四因中的特定原因而已。
[64] 同上,982b6-7
[65] 参见《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六卷第七章
[66] 参见《物理学》第二卷第二章
[67] 参见《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一卷第一章
[68]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第十卷601c-602b。
[69] 关于柏拉图技艺观的复杂性,参见《政治家》中罗列的各种技艺。他将“政治”这个亚氏那里属于“明智”的活动同样置于“技艺”之下考察。
[70] 参见《物理学》199a1-20,并《尼各马科伦理学》1140a
[71] 《形而上学》第五卷第四章,并《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末
[72] 参见《物理学》同上。
[73] 参见《物理学》192b14。此处指种类意义上的自身。
[74] 同上,193b9
[75] 参见193a32-34。注意此时亚里斯多德已开始偏离了上文的结论——自然是自然物同类的动因,而技艺则与制作物并不同类。
[76] 参见,同上,194a22-28
[77] 同上,199b18-20
[78] 参见《形而上学》1015a5-19。并《物理学》199b31-33
[79] 参见海德格尔,《路标》,页341
[80] 参见《形而上学》第七、八卷
[81] 参见《物理学》199a10-20
[82] 同上,194a35-194b1
[83] 此两重目的据牛津本翻译为“所指向”与“所为”,见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ed by J.Barnes, Princeton 。University,1995,Volume One , p332。又参见《形而上学》1072b2
[84] 合参《尼各马科伦理学》1094a10-15并《物理学》194b1-9以及《理想国》第十卷601c-602b。亚里斯多德的推进在于,确认了使用技艺认识形式,制作技艺认识质料。这样技艺之间的主导-从属关系就转化成了形式认识与质料认识之间的关系。
[85] 参见柏拉图,《政治家》??政治家统治这种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最典型的“明智”或实践,柏拉图也归诸“技艺”。
[86] 《尼各马科伦理学》1140b15
[87] 这种强调动力因中根本没有与目的之本质联系,因此有宇宙游戏者含义的解释,可特别参见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06,页码 104,108。海德格尔对动力因的此在式解释其实源于尼采。但尼采的这个解释本来就是亚里斯多德的旧意,参见《形而上学》1075b5-10。
[88] 参见柏拉图,《菲多》,97b-99d
[89]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之日喻,505a-509c
[90] 参见柏拉图,《蒂迈欧》28a-30d,Plato,Completed Works,ed by J.M.Cooper,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pp1234-1236
[91] 参见《物理学》199b30
[92] 参见《形而上学》1075b10
[93] 例如从巴门尼德开始,运用noein(思维)这个概念。参见,H.Diels(ed.),revised by W.Kranz,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Berlin 1961。第一卷,S238。
[94] 《形而上学》,1072b18-30
[95] 同上,1074b33-35
[96] 参见亚里斯多德《论灵魂》第三卷第四章以及第六章。
[97] 参见《论灵魂》429b29-430a1。合参《形而上学》以“存有”(“是”)融摄“一”的论证,见1003b24-35。并所思之复合与单一问题,见1075a6-10。
[98] 参见《论灵魂》430a15-19。
[99] 《形而上学》,1028b4
[100] 参见同上,第十二卷第一章
[101] 参见《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第六章
[102] 参见《物理学》第八卷第八、九章。合参《形而上学》1071b10-11。
[103] 参见《论灵魂》430a2-4,特别是430b6-23。合参《形而上学》1075a7。
[104] 参见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9,第六册,页2388
[105] 参见《论灵魂》430a1-2
[106] 通译为“分离的【努斯】”与“被动的努斯”。参见《论灵魂》430a22-25。
[107] 参见H.Diels(ed.),revised by W.Kranz,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Berlin 1961。第一卷,DK25,S135
[108] 参见同上,S238f。
[109] 参见丁耘,《是与易》,载《儒家与启蒙》,北京三联书店,2011,页278-281
[110] 参见《孟子.尽心上》,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11] 《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页274
[112]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二十五章。见《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99,页63
[113]参见《物理学》第八卷第八、九章。合参《形而上学》1071b10-11.
[114] 五行同样是依据“德”确认的“行”,而不仅是五种东西。如水曰润下,火曰炎上等。参见《尚书正义.洪范》。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0
[115] 《周易.说卦传》
[116] 从形指示德,就是《繋辞传》所谓“形而上之谓道”,详见《是与易》. 载丁耘,前揭,页码285-294
[117] 《周易.繋辞上传》
[118]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8,页560-561
[119] 李道平,同上,页560
[120] 同上
[121] 《中庸》,第二十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22] 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民书局,2004,第二册,页62-69。张岱年持近似思路。其《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唯独为“诚”出两条目,分别列于“自然哲学”与“知识论”之下。又于前条下列“诚”有“道德境界”意。实有三义分疏。见氏著《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100、232
[123] “诚,信也。”,“信,诚也。”,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1981页92下。
[124] 《中庸》第二十五章
[125] 《周易正义》,孔颖达疏
[126] 《中庸》第二十六章
[127] 《周易正义.坤.彖》
[128] 《周易正义.乾.彖》
[130] 《繋辞上传》
[131] 《周易正义.乾.象》
[132] 《中庸》第二十六章
[133]“直方大”,见《坤.六二》。《庸》之“悠久”、“无疆”,即《易》之“久”、“大”。所谓“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繋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同上)。则“可久”即日新,乾元之德。
[134] 《周易.序卦传》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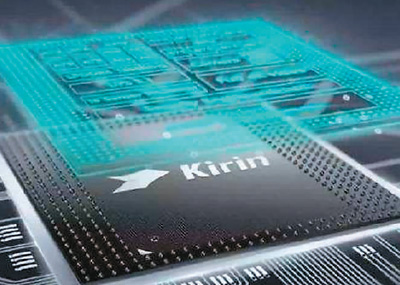
 001
001
 002
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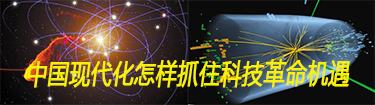 003
003
 004
004
 推荐席位
推荐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