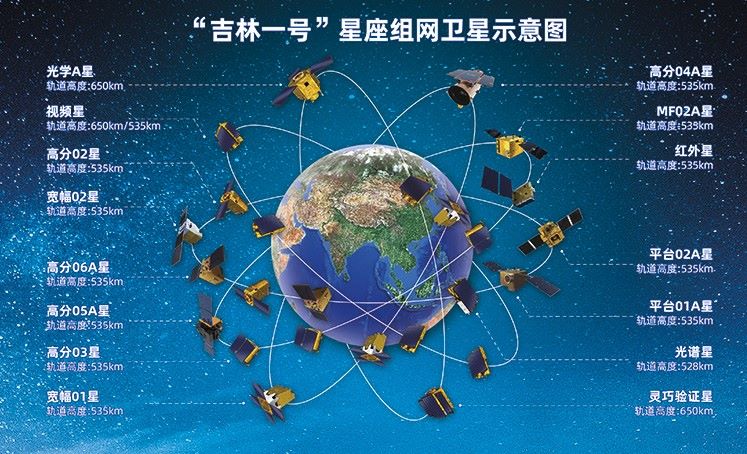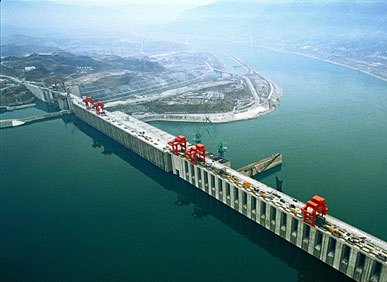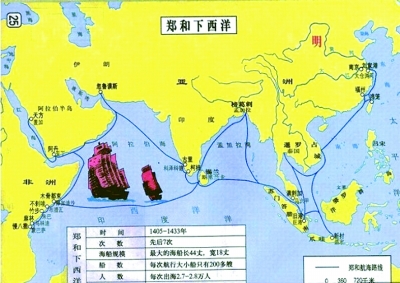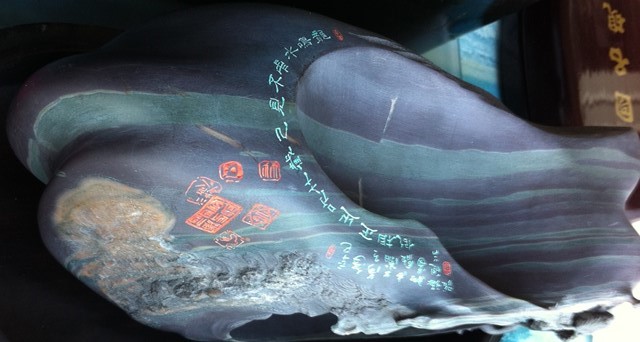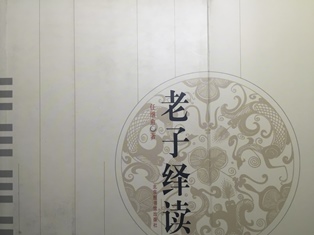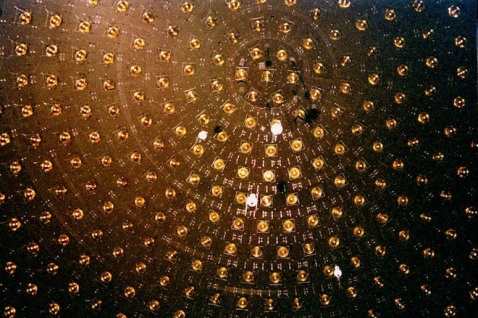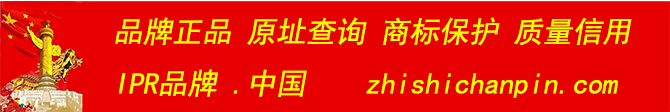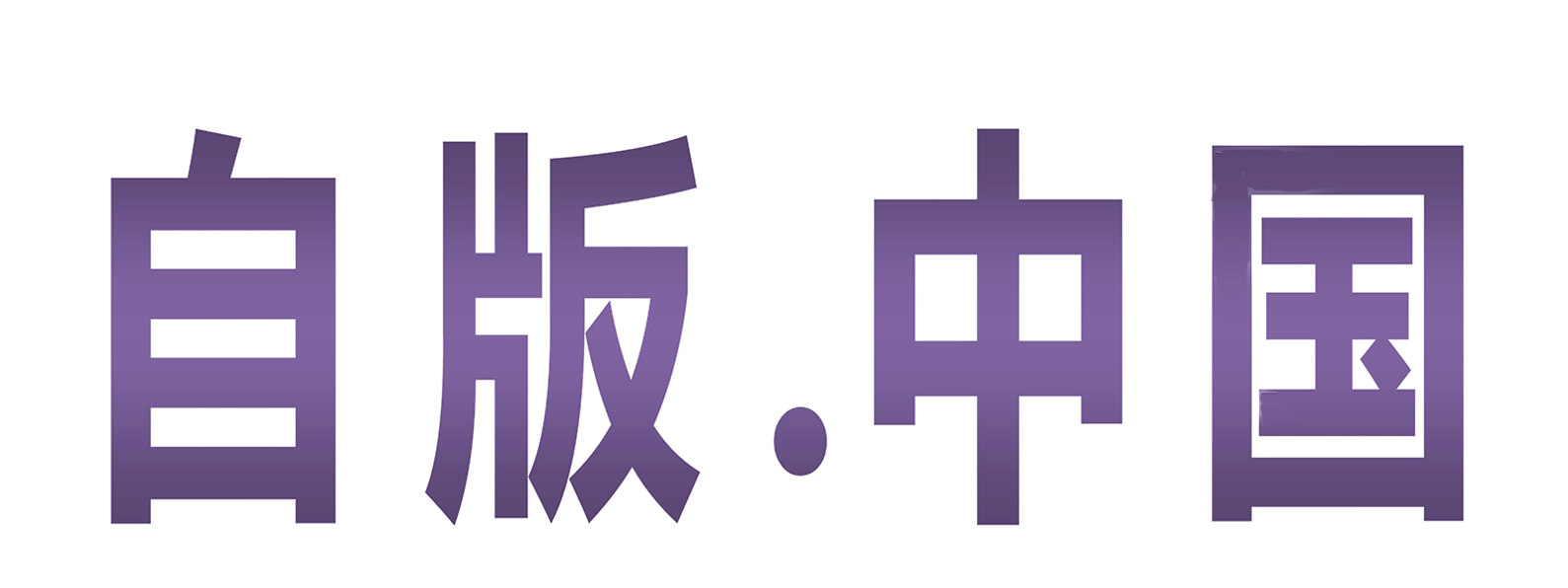“匍匐”生存
作者:刘照进
2004年冬天,我将散文《匍匐》投到某省级文学刊物,不久后我打电话给编辑部了解稿子的处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可以用,但要修改。编辑老师建议我将题目换掉,而且内容也要改得明亮一些,说我原先的稿子过于灰暗,并且暗示我生活中不乏亮点。这让我陷入两难。一方面,我固然希望能够发稿(甚至是渴望),另一方面,我又不想单纯因为发稿而改变我写作的初衷。有关《匍匐》一文,我只是将我的秃笔插入到生活的底层,在那里挖出了真实的煤矿。它原本就是灰褐色的,带着灰暗的色彩,无法给人以拔高的启迪和朗照的信心。但我相信它的真实能够带给人强烈的震撼,远比那些号子似的歌咏有力量。这不得不让人警惕:文学的“样板化”依旧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不明白,难道文学除了在向艺术的高峰靠拢之外,面对苦难它还需要绕道而行吗?或者对现实进行巧妙的伪装甚至改头换面?在世俗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更多人心里的文学概念是什么呢?难道是涂着政治口红的浅俗图解吗?
权衡再三,我最终抵制了发表的诱惑。好在稿子终于被其他杂志刊用,这多少是对我固执坚守的一种安慰和鼓励。
事实上,我一直喜欢“匍匐”这个词。我喜欢它卑微、卑小、卑怯甚至卑琐的气质,它所包容的民间的隐忍和沉默。直至今天,它内心的渴望和疼痛依旧被简拙的外衣包裹。这是贴近大地较为真实的行走,它们的存在似乎天生就被人忽略。很多时候,匍匐,它已在我心中结出泪水的藤蔓,我的怀旧和感恩通过时光隧道回到劳动的田野。就像粮食家族中的玉米、红薯、土豆这些低矮植物一样,尽管它们一直以灰扑、粗砺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眼中,而且容易受到忽视和轻慢。但我喜欢。这或许与我的出生有关。我的家乡一年四季只生长玉米、土豆、红薯,它们的身上带着劳动的伤痕和农家肥的气味。一粒粮食从田间走到餐桌,它要通过多少汗水的洗礼,而劳动者匍匐的身影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水稻似乎应当算作众多粮食作物中的贵族,它一直那么纤柔,果实白净、饱满、晶莹剔透,仿佛细小的玉粒。那是不是众多的人一直追逐它的理由呢?我不得而知。但我同样不喜欢它过分的细腻、素雅,书生气太浓,贵族气太厚。尤其是它择地而生的性格,有些让人感觉娇气十足。它需要足够的水分滋养,喜欢平坦,追逐肥沃,拒绝干烈、高坡和贫瘠。而玉米、土豆、红薯却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它们只能选择高坡、贫瘠、无水的土地,把根扎下去,艰难地生长。这是玉米、土豆、红薯的命运。它们同样也向往平地,渴慕水足地肥,但没有选择的权利。
有时候,我这样想:人其实就是一种植物,水稻,玉米,红薯,土豆,或者别的什么。其实大家当初的命运都相差无几,共同处在种子的起跑线上。但是,却被冥冥中的一阵风或一双手撒向了不同方向。到了后来,彼此的境遇就有了不同,就在成长之后忘记了童年的时光。一棵树长大之后,总是高高在上,它的眼里只有无限的天空和太阳的光芒。它忽视了自己的出生和生命的弯曲。
现实中,我见惯了藐视,见惯了大树似的轻慢和狂妄。他们缺乏对匍匐者的关照和悲悯情怀。他们的骨子里流着清高者的血液,潜伏着藐视的因子。民工的工资可以无限期地拖欠,对衣衫褴褛者任意施以无情的谩骂,对伤残老弱者的躲避和漠视……一个道德和良知、道义缺席的现场,我不知道,面对被遮蔽的天空,一株匍匐的矮小植物,它的仰望能不能够按期抵达。
如果文学是安放灵魂生病的床架,是对病痛的拯救和疗伤,除了美学,它还有更多的责任担当,那我们就不应当拒绝“匍匐”生存的一切。
转载:求是 (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