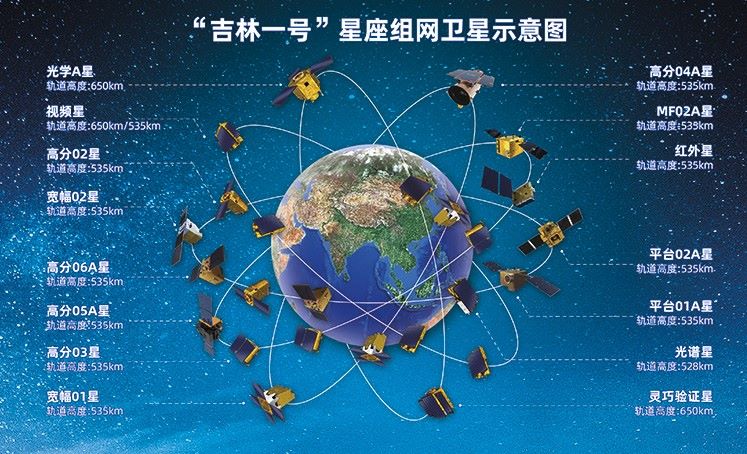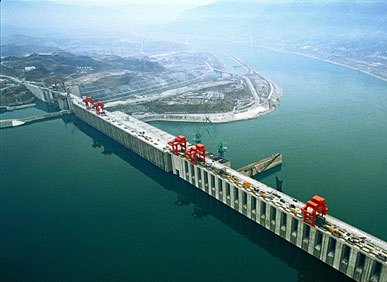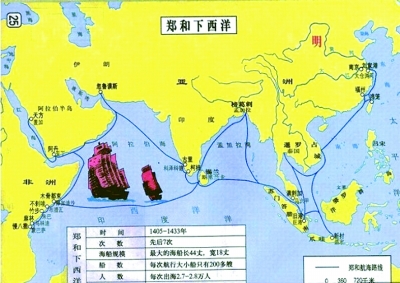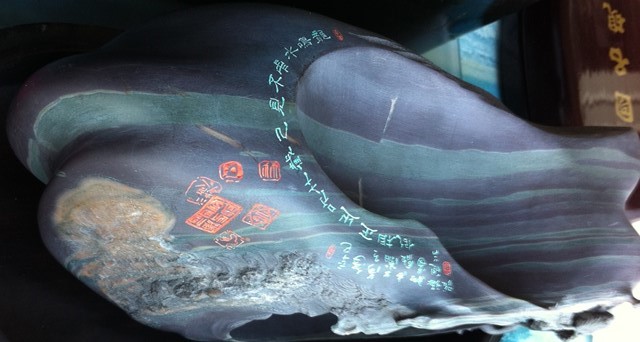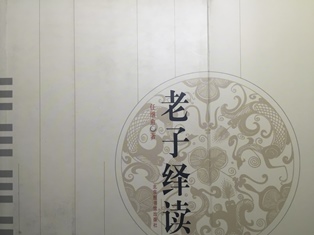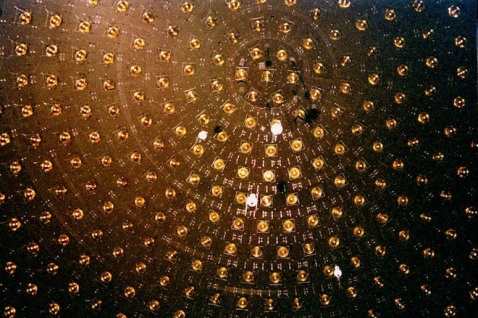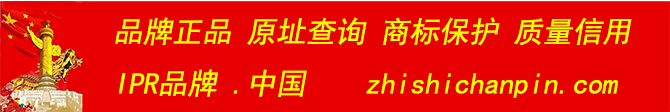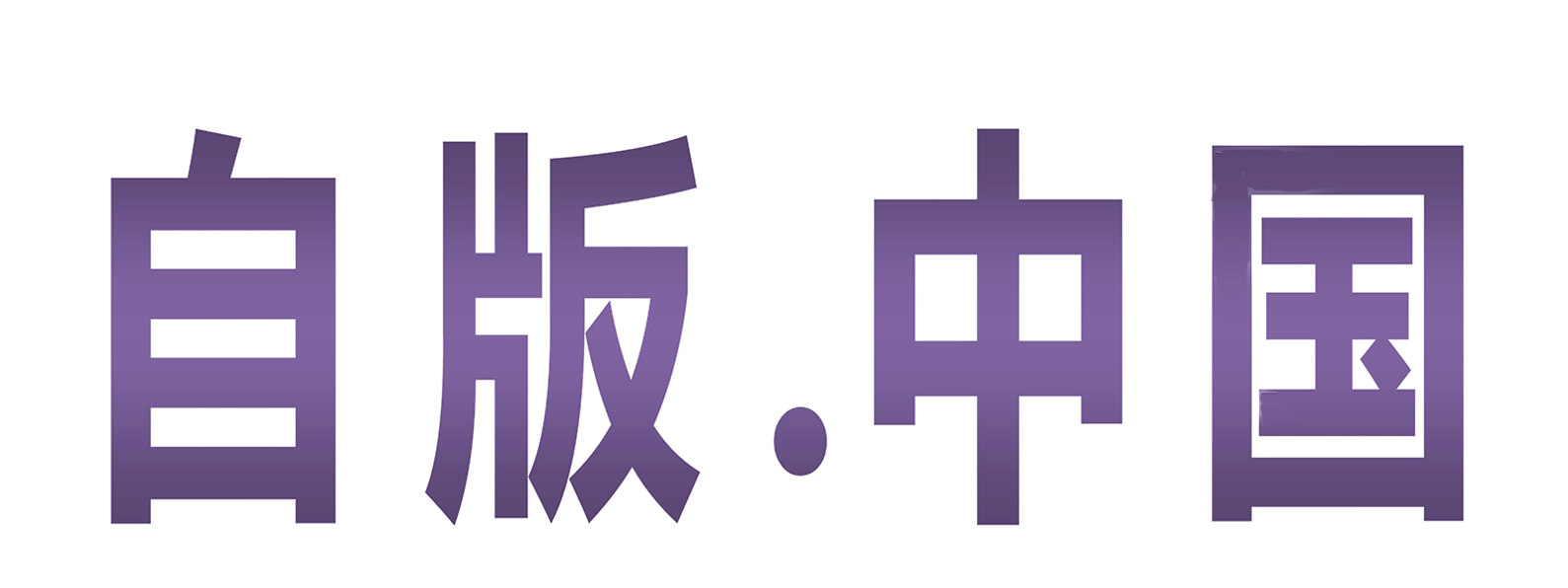追问悲剧的根源
作者:王春林 张玲玲
虽然已经过去了半年多时间,但发生在2010年3月28日的那场王家岭矿难,人们依然记忆犹新。在电视以及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都已经全面立体地报道过王家岭矿难之后,山西省作家协会的赵瑜等五位作家为什么还要再次对于这一事件及相关当事人进行深入的采访,并且要写出《王家岭的诉说》(作家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这样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呢?
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种就是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等遵循的现象真实,另一种则是报告文学作家们所欲探寻的更深层次的本质真实。报告文学从本质说其实是一种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写作。对于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说,他的写作目的并不仅仅只是对于表层事实的客观呈示,更是对于事实成因进行一种深层次的思考与追问。赵瑜等五作家进行《王家岭的诉说》的写作,其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五作家通过分头采访、材料共用,最后由一人统一撰稿的方式,完成了对王家岭矿难的叙述。以其新的表现形式及深沉的理性沉思力量,再一次构成了对于我们心灵世界的强烈冲击。当发生在矿难中的那些令人或同情、或感动、或悲愤、或沉思的画面和声音业已被新的新闻材料、新闻事实所取代,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鲁迅所谓国民的“健忘”本能悄然发生作用时,这部报告文学以一种画面和声音替代不了的独特品质证明着人间灾难的存在,证明着矿难中无数生命的陨落。作者们以一种不懈追问的方式,把此次矿难事故放在了历史的坐标系上来加以书写。随着阅读进程的步步深入,生活中那些假相的面纱开始被层层剥离,矿工(其实都是来自于乡村的打工农民)艰难的困窘处境渐渐变得公开,成为了一种不无荒谬色彩的真实,冲击着读者的情感底线。与那些新闻媒体所做的报道相比较,可以说,这样的书写更让我们感到震惊,更能够引发我们的深思。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在这里当然不可能全面论述《王家岭的诉说》的深层价值,但赵瑜等人以王家岭矿难为切入点,对于近百年来中国矿难史所进行的深入反思,却有着令人振聋发聩的思想艺术效果。在我看来,作家们首先追溯到发生于1949年的山东淄博矿难,然后再追溯到发生于“文革”期间的大同老白沟矿难,其意图正在于借此而对矿难近乎于相同的成因进行有力的探询与反思。只要简单地联系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这几次大矿难的成因,实际上都与我们的领导者不顾客观规律,漠视矿工生命,一味盲目地追求进度和产量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关于这一点,赵瑜他们在作品中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如果说,此前发生的两次矿难的成因,更多地与当时的激进政治存在着紧密关系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王家岭矿难实际上就是过分追求经济效益所导致的严重恶果。无论是政治也罢,还是经济也罢,归根到底,还是对于普通人生命价值漠视的结果。能够把王家岭矿难提升到这样的一种精神高度来加以思考和认识,体现出五位作家的理性力量和深刻真诚的悲悯情怀。
很显然,如果更进一步地追问下去,自然就会涉及到我们这个现实社会更加内在深层的社会机制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作品中所举出的一组数据,就不难得出相应的结论来。“我国的百万吨死亡率为2.4,即每产200万吨煤,要死5个人。这一比率高于印度10倍,高于俄罗斯50倍,高于美国100倍。我国每年实际死于矿难人数7000人,美国则在30人左右,在许多国家,某些年份已经达到‘零死亡’。”必须承认,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既是残酷的,同时却也是真实有力的。这样一组可谓是反差极大的数字对比,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结论其实已经不需要再说出来了。在赵瑜等五作家合著的这本《王家岭的诉说》中,我们再一次真切地领受到了报告文学所具有的理性沉思力量。
在被《王家岭的诉说》感动的同时,我们也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关于中国矿难的沉思之中。尽管已经有过无数次的沉痛教训,但是我们的矿难为什么还是频繁发生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彻底地与矿难诀别呢?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