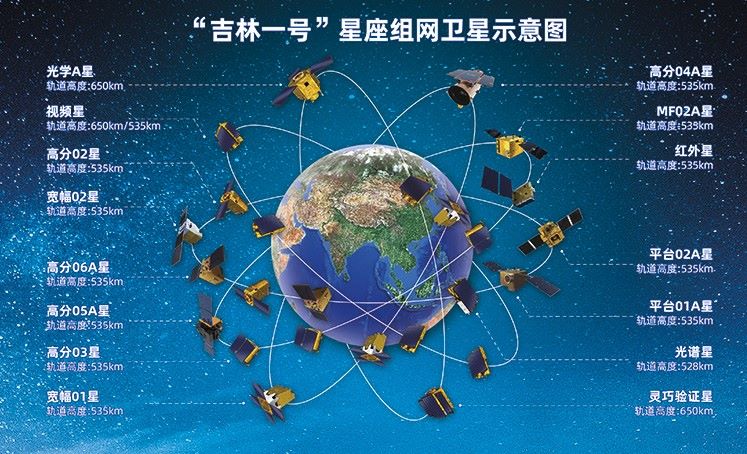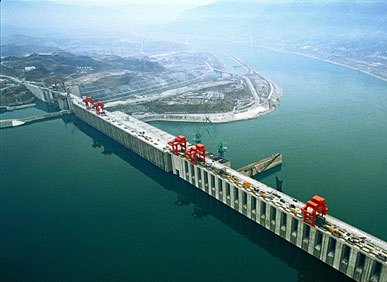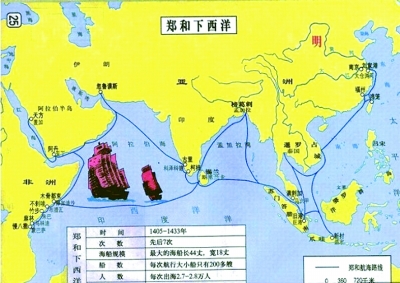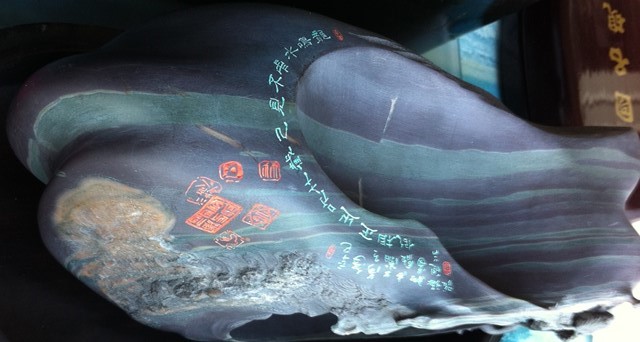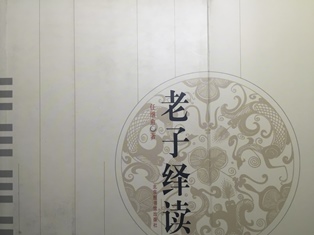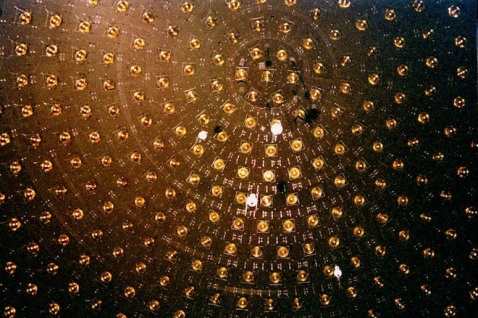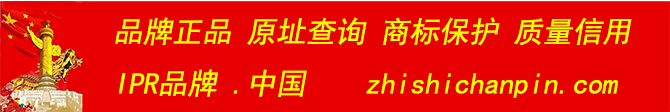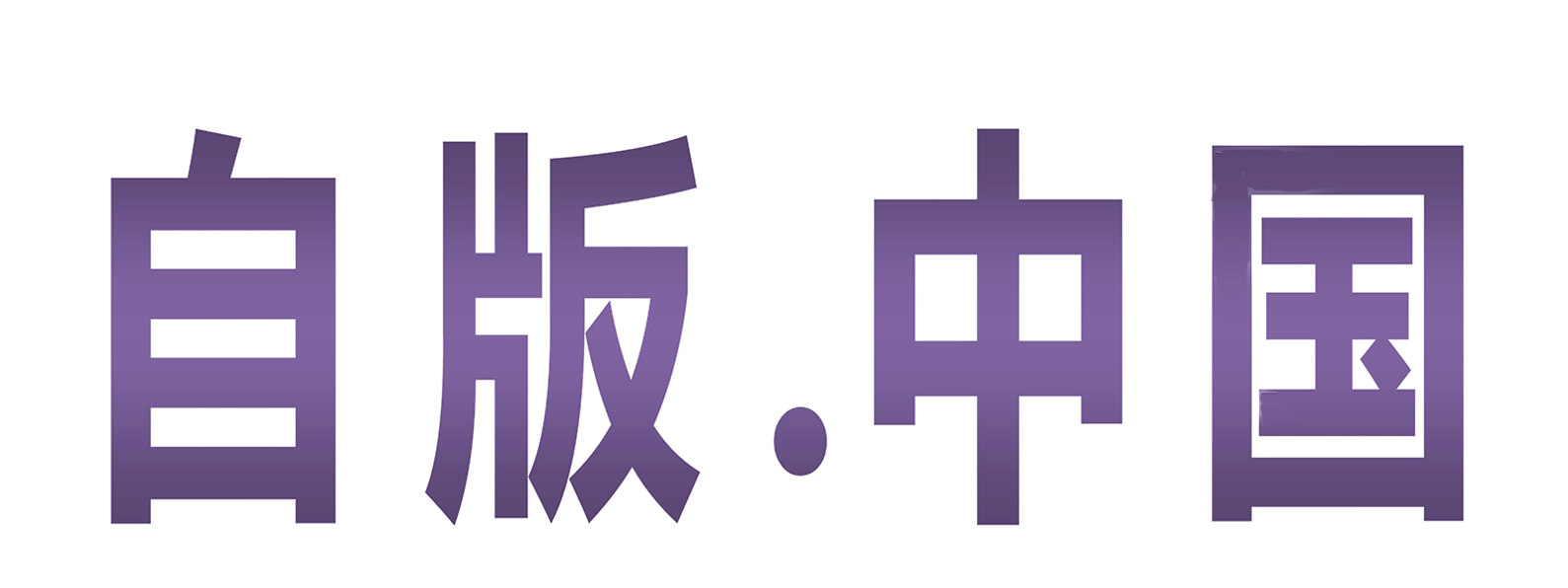当美丽穿越了时空
作者:徐芳
东晋文学家干宝,曾在《搜神记》中,只用了淡淡几笔说它:“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 ”
从 “不知”然后 “知”;由“得”而“不得”,又由“得之”而“亦得”,其中过程,有波澜,有曲折。而干宝所使用的信口而出,率然天真般,却又并不一泻而出的口吻,也仿佛是我在这一路上过目而走心的话语断续。
豫章乃江西的旧名,新喻如今叫做新余。新余仙女湖,当然得名于此则神话。虽然大小仙女已不知何处去了,豫章新喻男,也不知在此经历了几世几代,几千载。时光倥偬,山光、水色、小岛,却仍浑然不觉。看我摇荡的眼波,既像贴着地面伸延,却仿佛还倒映了广大的天空。 “天际线”与“水际线”,大概就这样相连与交错了吧。
山峦重重叠叠,却又都不险要。青螺似的一座座小山,不峻拔,不伟岸,可当路引路,路转路时,这才让我们真正知道了山之深、山之幽。此地多松、樟、油茶等,红泥中盘根错节的,常常不知是一棵树,还是多棵树,皆一堆堆尽抱成了树团。而哗哗流淌的瀑布,一溜大大小小,像布,像绸,像纱,像练,不知多多少少,过山过岩,过江过河,流逝又不流逝的样貌,或者说:是流而不逝的守望。
几次突然消失在眼前,又再几十次贸然地撞入了眼帘的,除了鹭鸟,就是一股又一股横逸斜出的水。有时候,一只鸟,一道涌水,就像从胳肢窝里呼啦啦地冲出,说不清,更看不清那前后、左右、上下。
看这看那,目不暇接,眼眶似有开裂的隐忧。这不是目光的速度,身体的敏捷与否的问题,而是心灵如何感应的问题。
我自问又反问:这若隐若现的鸟,还是鸟吗?可它难道不是吗?这神出鬼没的水,还是水吗?究竟是不是呢?
就像头顶上金黄色的银杏羽叶,一枝千叶、十枝万叶的,在晴空中袅袅地游荡着、飘荡着。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道天光,每一瓣浪花……似乎也都会飞,还会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直至彻底消失在天尽头。
有人每次转头看来路时,都觉得那是一个不言的惊奇。可能,他又怕它们会在转眼间,不打招呼而倏然消失吧?这实在是个容易让人迷失的地方。
以山相衬,与天相映,在水波如蛇行于脚底时,幸好,我是自己灵魂出窍的目击者:如光影般明灭不定的微风习习,一片片白羽毛般的云彩,升腾于山环水绕中;而我的脚步似乎已经离开地面,有一小会儿了,却仿佛仍是无着无落——那是徘徊而迟疑的悬浮状态。
当波光蔓延,翠色满眼之际,人面却迷离。而当我们借用手机的微光照明,用以走林中朦胧夜路时,却听见同行中,有个女孩尖声惊呼:“山要倒下来了! ”这也是“飞”起来的感觉吧?这个“飞”,当然不排斥她因胆怯而 “飞”,可同时,或许也包括了山“飞”,水“飞”,忽而昔年,忽而往古之“飞”!
当美丽穿越了时空,此刻,每个人可能都是“毛衣”飘飘的“仙女”,那也包括了我。仙气,或于斯可观。而当仙女不在,爱仙及湖,以及青山、蓝天、松、樟、茶树,都成了我流连与称颂的对象,用金圣叹的话说,是“大获我心而去”。
有个饶舌的朋友,此一路上,零零碎碎、啰啰唆唆的,解释着所谓的“灵异”现象:“风景不可呆看,有些不符合现实为最佳。在神话那里,即为超过。超过,也就是进一步地符合了现实……”总之,是反复申明要爱天赐,爱地赐,爱人,也爱神明。
我只有一再地点头称是,极是。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