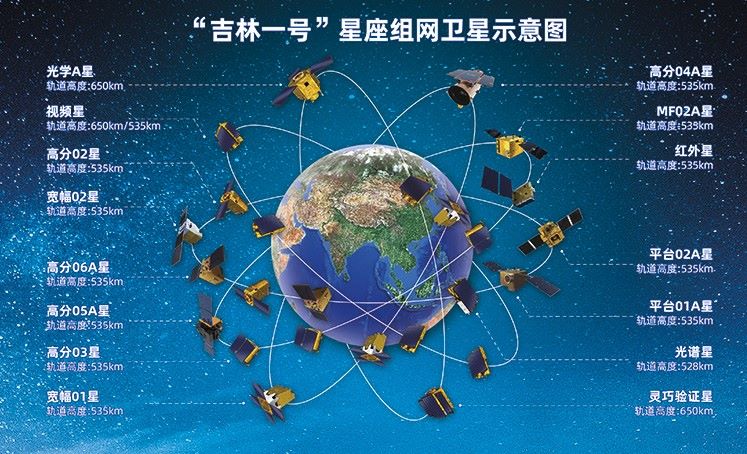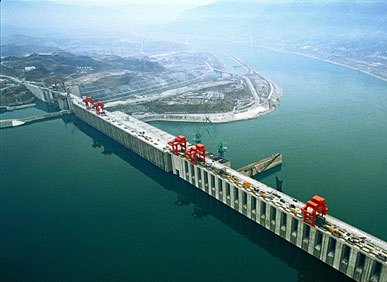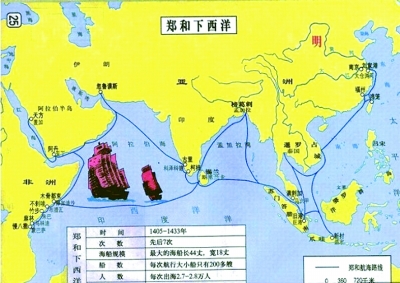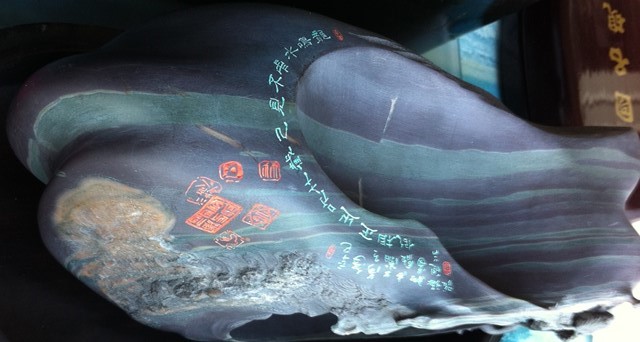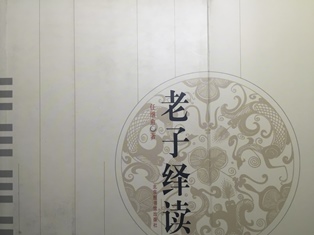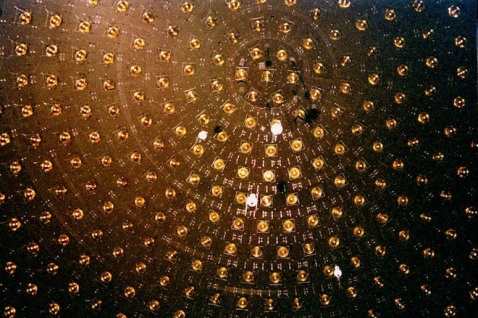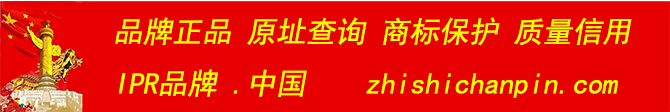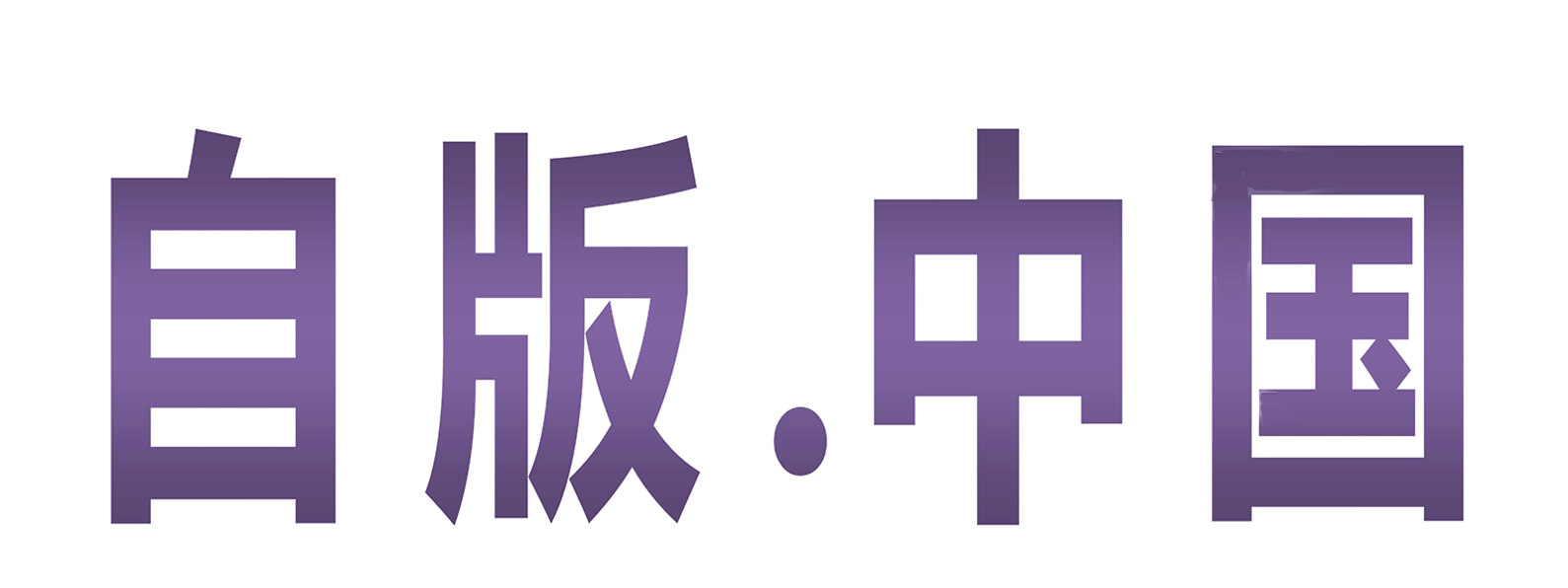灯
夜幕降临了,昏黄的街灯,稀疏的行人,断续的叫卖声。我一人独自在街道上游走着,说是街道,其实并不宽,若是遇上一两辆机动车呼啸而过,就得小心翼翼地靠到街道的边上,以躲避车辆扬起的灰尘。街道也不算太长,满打满算,也就区区两三公里的样子,更何况又只是一条直街。
临街边上立着一位卖烤红薯的老人,他脸上露出的慈祥与善良,让我感到亲切、温暖,他身旁的那盏煤油灯也同样让我亲切、温暖。它让我记起了小时候自己用过的那盏煤油灯。
20多年前,我在这里读初中时,这里还是荒僻的村落,其景况与翠溪村大抵没有什么两样,山峦、土地、古庙、磨房、古井,再加上百十来户人家,唯一多出的就是那座初中学校了。那个时候,街道还是土路,没有电,家家户户都用煤油灯。到了掌灯时分,庄户人家窗户上露出的亮光,朦胧、模糊,影影绰绰。这条土路上也是空空荡荡的,偶有一两个村人走过,单单听那脚步声与咳嗽声,就可判断出村人的名字来。最热闹的还是学校下晚自习时,学生结伴回家的情形了。宏亮的铃声响过不久,土路上便出现了三三两两的人影儿,有的人手里还把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灯上还罩着一个用纸糊成的圆筒,为的是怕灯盏被风吹灭,而临时套上去的。灯不大,做工极其简单:一个墨水瓶,瓶盖上竖插着一个铁皮卷成的小筒,里面是一根棉花搓成的捻子。这般简陋的油灯却是每个学生所必需的学习用品,晚自习的时间,每个人的桌上都会放着这么一盏油灯,样子大抵也是相同的。一阵短暂的喧闹过后,土路上便恢复了平静,一切又悄无声息了。
大约在我混沌初开之时,我便隐约明白了一个道理,白天里,正是有了日头散发出的亮光,人们的一切活动、劳作才有了依托,可到了夜晚,日头落下去后,那就只能依靠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了。尽管它是那么普通、微小,不足挂齿,发出的亮光也只能照亮几尺见方的空间,可正是因了它的存在,人们必要的起居劳作才能正常进行。靠着煤油灯昏暗的光亮,妈妈可以做上一阵儿针线活,哥哥可以写写老师布置的作业,闲不住手脚的爸爸可以干一些家务活。而在这样空闲的夜晚,我也会从自己的小抽屉里取出几册连环画,漫不经心地翻阅一阵儿。几乎是每夜每夜,我常常就这样子忙碌着,有的时候,不知不觉间,就倒在炕头睡过去了。现在想起煤油灯与连环画相伴的那个岁月,心里总觉得那真是一段温暖、亮堂,颇有意味的日子。
有一回,是深夜,爸爸提回一盏精巧别致的灯,灯的上下都是铁皮做的,中间夹着一个圆圆的玻璃灯罩儿,里面发出的光,亮亮的,要比我家的那盏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亮出许多许多,我好奇地问爸爸,哪儿弄来的这新式玩意儿?爸爸笑着回应说,这新式玩意儿叫马灯,是工厂里做出来的,咱村子里统共也就那么三四盏,都是特别留给喂养牲畜的几个大叔用的,他们深更半夜还得出来给队里的牛儿、马儿添加草料,这玩意儿雨浇不着、风吹不灭,深夜里外出办事,带着它会方便许多许多的。这盏马灯就是爸爸从村子里一个饲养员大叔那里临时借来的,改天还得再还回去。我向爸爸探问起马灯的价钱,因为我想让自家拥有这么一盏马灯。爸爸似乎听出了我的意思,说道,这玩意昂贵得很,咱家是买不起的。我伸出双手,轻轻把马灯托起来,睁大眼睛观赏着、把玩着,仿佛对待宝贝一般。放到炕头的中央,抬头一瞧,屋子里顿时亮堂了许多。
上小学时,爸爸特意给我做了一盏煤油灯,那样子与家里用的那盏煤油灯如出一辙,所用的原料也一样简单,一个空墨水瓶,一个小铁筒,一根棉花揉成的捻子。这样的东西简单、便宜,家家户户都可以弄到手的。和我一起学习的十几个小孩子人人都有这么一盏煤油灯,上晚自习时分,十几盏小煤油灯一起点亮,每张小脸也被映照得红扑扑的,就连教室四方也不显昏暗了。时间一长,每个小孩子的鼻孔都被煤油烟熏成黑乎乎一片,流出的鼻涕也变了颜色。老师见状却笑着说,煤油烟熏黑了鼻孔是没事的,熏黑了脸膛也无关紧要,肚子里能学到知识,长大就会过上好日子的。老师略带俏皮的话语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不巧有一次,一个小女孩的头发被煤油灯火燎了一些,当时,这个小女孩便大惊失色,呜呜啼哭起来。小女孩身旁一个爱打趣的小男孩,这个时候便将老师的话语略加修改,一本正经地说道,头发让煤油灯火燎掉也是没事的,肚子里能学到知识,就是好样的,长大后可以过上好日子啊!小男孩的调皮同样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个时候,小女孩赶忙用双手捂住脸,哭啼的声音更响了。
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女教师,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盏灯,灯罩与灯体都是用玻璃做成的,那样子与马灯一样的精巧、别致。有一回,女教师让我帮她扫地,借着这个机会,我便靠到灯的近处,只见圆鼓鼓的灯体里是略微发黄的煤油,一根白白的灯捻子横卧在里面,玻璃灯罩的两边小,中间部位如同鼓起的肚子一般,大大的。我只是用眼睛细细地端详着灯的每一个细部,却不敢伸出手摸一摸,生怕一不留神,弄坏了灯体,惹下大祸,引来老师的严厉批评。想一想夜晚老师窗户上发出的亮光,要比普通庄户人家的亮出许多许多,我不由暗暗惊叹这盏灯的神奇威力。回家后,我便绘声绘色地向爸爸描述起来。爸爸听完后,笑着说,这盏灯叫罩子灯,也都是从工厂里制作出来的,与马灯一样的昂贵、稀罕。在翠溪村里,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盏,大约也只有老师的办公室、大队的办公室才可以用上这样的罩子灯了。
后村的一孔窑洞里,住着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奶奶,老人家一直习惯用麻油灯盏儿照明,儿子特意弄了一盏煤油灯,她却搁在一旁不用。比起煤油灯来,麻油灯盏的用法更是简单而方便,只要将麻油倒入灯盏,再放上一根儿棉花捻子,就可点着照明了,麻油也是老人家自己一点一点磨制出来的,一切都是自给自足。那个灯盏儿都是用瓷做成的,从上到下是一个整体,表面呈漆黑色,透亮透亮的,闪闪发光,样子古拙、大气,它的性状与我曾经见识过的马灯、罩子灯截然不同,二者是不能放在一处相提并论的。看着老人家的这盏灯,我也不止一次暗暗惊叹过。老人家屋子的墙壁上漆黑一片,有人说,那就是麻油灯放出的烟雾熏黑的,可我却一直怀疑这话的真实性,总是固执地以为,那漆黑的墙壁大约是天地造化的结果。掌灯时分,我还专门注意过老人家的麻油灯,它释放出的亮光似乎要比我家的煤油灯更强一些,我还专门注意过老人家的面孔,慈祥、安稳,就像那盏麻油灯一般,让人温暖,让人领略不尽。宋大伯所讲的传奇故事里,说书人赵先生讲唱的精彩段子里,也出现过麻油灯之类的词儿,我便不由将二者联系在一处,心想,老人家这盏麻油灯的背后或许也有一些精彩的传奇故事,与宋大伯讲出的、说书人赵先生说唱出的大约是一样的精彩而迷人。我还特意向爸爸发问道:麻油灯的灯光要比煤油灯亮堂一些,用起来也简便、省事, 也省钱,麻油自家就可以磨制出来,用不着跑到商店里,购买昂贵的煤油啊!可为何所有人家反而用起来煤油灯呢?面对我的发问,爸爸停顿了一会儿,微笑着回应道,这其中的道理我也说不清楚,或许是年代变了,麻油灯不再时兴了。翠溪村里,家家户户都用煤油灯,如果咱家点上麻油灯,世人会笑话的。而那个老奶奶就不一样了,她人老了,一切全无所谓啦!爸爸的话儿似懂非懂,感觉他是随意说出来,搪塞我的发问而已。
等到翠溪村里有了电灯时,我已经在县城的中学里念高中,偶尔回家短暂住上一两天。翠溪村的村前村后,矗立着几根儿高压线杆子,空中盘绕的则是一根一根的电线,东一段、西一段,而家家户户的屋子里也多了一个用来照明的普通灯泡。看着这样的情形,我便觉得翠溪村真是变了模样,似乎更加洋气一些了,而过去存在的古朴与温暖则消退了不少。这个时候,重新想起过去年代里的煤油灯,我觉得那个年代猛然间遥远了许多、许多。而想起那位老奶奶家里的麻油灯,我更是感慨万分,仿佛那已经是极其地古老了,就像宋大伯讲述的故事、说书人赵先生说唱的段子,一样古老,一样遥远。
一天午饭后,在家里一个大木箱内随意乱翻书本时,无意当中发现了一盏马灯,还有一盏罩子灯,马灯的表面已经是锈迹斑驳,罩子灯灯体的玻璃表面也满是灰尘。看着这两样已经过时,废弃不用的玩意儿,我就自然想起了小时候把它们当做宝贝儿对待的动人情形。使用麻油灯照明的那位老奶奶早已过世了,而用罩子灯办公的那位女教师也离开了翠溪村,当下的具体情状我一无所知。晚上吃饭时,爸爸打开了开关,屋子里顿时一片亮堂,看着闪闪发光的灯泡,我又禁不住想起了麻油灯、煤油灯,当然也想起了一度被自己视作世间物品的马灯与罩子灯——马灯是爸爸偶然带回家的那只,罩子灯则是女教师办公用过的那只。这个时候,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在我的心间流动着、漂浮着。
当我向父亲提到木箱里的马灯与煤油灯时,他只是淡淡地回应说,那是我从学堂的院子里捡回来的,村子里已经有电灯了,这玩意儿成了过时的东西,把它捡回来,当成废品,或许能卖几个钱。以前的煤油灯,更是没用了,龙王庙前的沟渠里,东一只、西一只,小孩把它当成玩具,踢来踢去,咱家的地畔上我也见过几只,那迟早会被雨水冲走的。听着父亲的话语,我不由感到惋惜。晚饭后,我在屋子里翻弄起来,想找出家里以前用过的那盏煤油灯,可最终只是白白忙碌了一阵子,那只煤油灯早已不知去向了。看来曾被我视作稀罕珍品的马灯与罩子灯无疑是没落了,而早已在翠溪村没落的麻油灯,当下更是绝迹了,见识过它的人们,大约只能凭记忆感觉其古拙与素朴的意味了。
回到学校后,又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可在空闲之余,或在夜深人静之后,总会记起那些式样各异的灯儿——麻油灯,马灯、罩子灯,还有煤油灯。这个时候,过去年代里的一些人事也会随之在脑海里浮动着,爱讲故事的宋大伯、说书人赵先生、坚持点麻油灯儿的老奶奶,还有那位严谨和蔼的女教师,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素朴、本真让我温暖、亲切。之后,我上了大学,又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可这几只素朴的灯,这几个素朴的人,一直真真切切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成为了这个灰色尘世里一束亮光,与我相伴,给我信念。
来源:人民日报